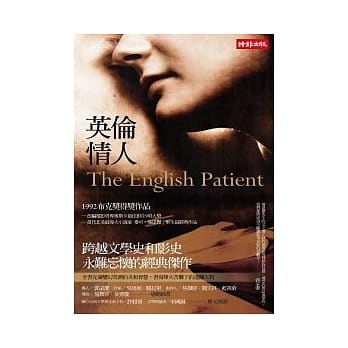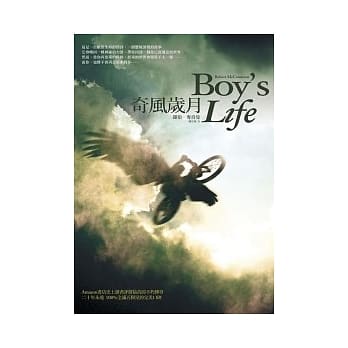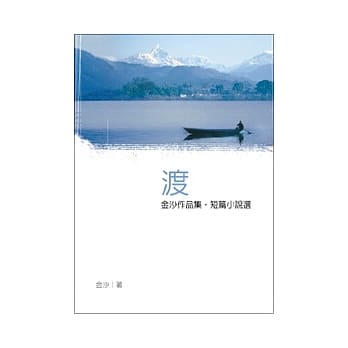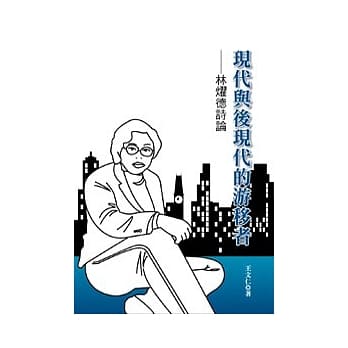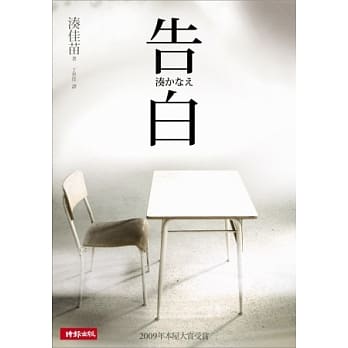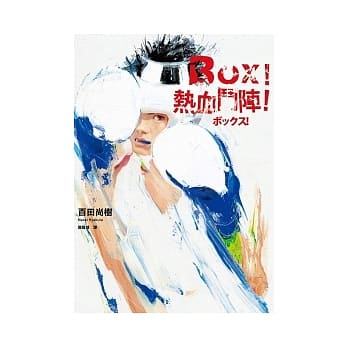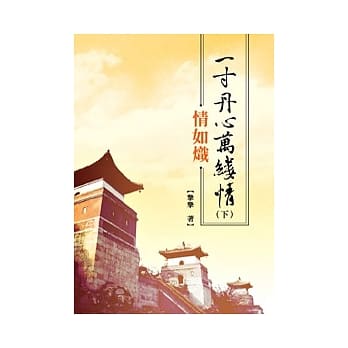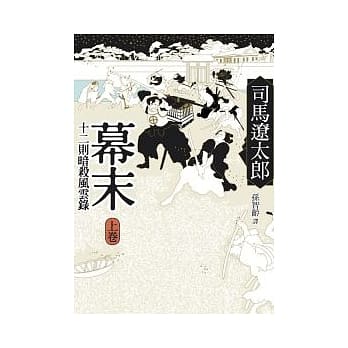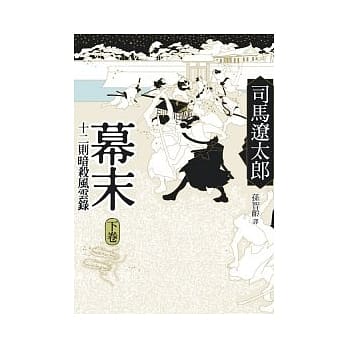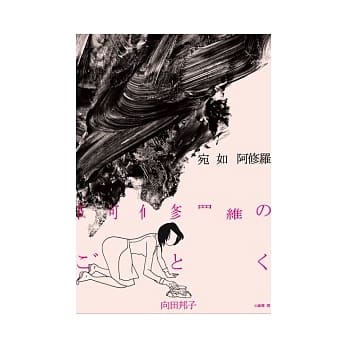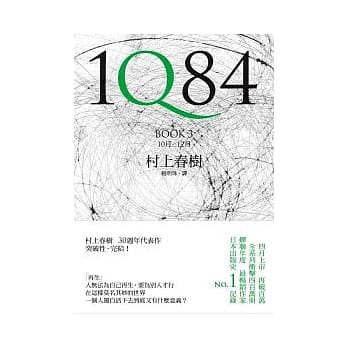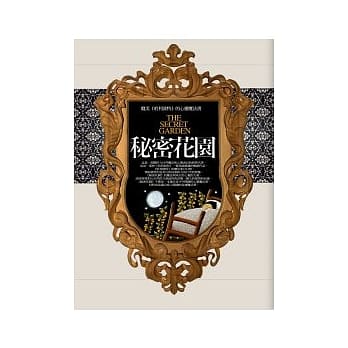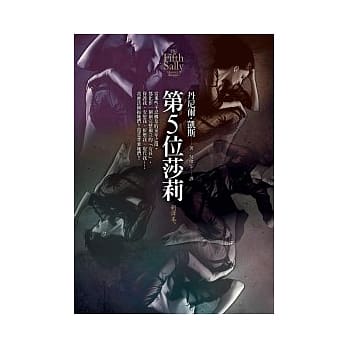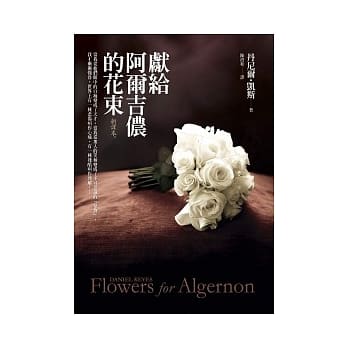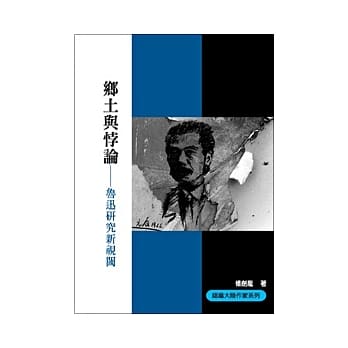圖書描述
我的手捧著世界文學瑰寶,但我的工作是親手銷毀它。
沒有筆的作傢,形同靈魂已死;被抹去記憶的人,等同失去希望
在1939年的莫斯科,曾為文學教師的帕維爾現在的工作是要銷毀政府當局視為有問題的手稿。
帕維爾沒想到他得親手焚毀在課堂上教過的文學經典,加上朋友不明的失蹤,妻子死於意外後,連屍體也不得見,伴隨著失智癥的母親,帕維爾覺得人生幾乎快完瞭。
一箱箱將要被焚毀的書籍與手稿,活生生的承載著人類的心靈,同時又如莫斯科寒鼕的微弱火光,命運如此的渺茫;當帕維爾親眼見到寫過《紅色騎兵軍》的作傢巴彆爾,在監獄裏被摺磨得不成人形,帕維爾知道,得想辦法保護巴彆爾僅存的兩捲手稿瞭。
保護巴彆爾的手稿,意謂也將承受失去生命的風險,帕維爾能選擇不要燒毀擁有夢想與靈魂的紙張嗎?如果像他的母親擁有生命,卻失去過往,人生又有意義嗎?在無盡的疑問中,他的手裏握著巴彆爾的兩捲手稿、失蹤朋友留下來的情書、來往的信件,那些承載記憶與故事的一切,是如此的脆弱,但也唯因為擁有靈魂,纔能讓他感覺活著,他該選擇為巴彆爾的手稿做些什麼瞭……
作者簡介
崔維斯.賀蘭 Travis Holland
崔維斯.賀蘭的故事散見於《微光列車》、《五要點》、《犁頭》等刊物。他曾兩度獲得「霍普伍德奬」,並擁有密西根大學的美術碩士學位,現居密西根。本書為他的第一部小說,2007年同時榮登為Publisher's Weekly 和Financial Times年度暢銷書,以及Guardian Readers選書。2008年榮獲維吉尼亞州立邦聯大學的卡貝爾小說新人奬。
譯者簡介
張琰
颱大哲學係畢,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現為專業譯者。譯作領域廣泛,有《比利時的哀愁》、《西班牙情人》、《穿風信子藍的少女》、《愛情的盡頭》、《賈斯潘王子》、《萬物的尺度》、《蝴蝶法則》、《蜂鳥的女兒》、《12號公路女孩》、《悲喜邊緣的旅館》、《我的愛,說不齣口》等。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推薦序1
曾經存在過就不會被遺忘……
熊宗慧(颱大外文係助理教授)
美國作傢崔維斯.賀蘭(Travis Holland)的作品《最後的手稿》(原名為The Archivist's Story),是以一九三○年代史達林大清洗時期的俄國為背景,描寫一個在蘇俄內務人民委員會(即NKVD)辦公處──盧比揚卡大樓(即後來的KGB總部)工作的檔案員帕維爾,冒死將猶太裔的俄國作傢伊薩剋.巴彆爾(Isaac Babel,一八九四 ~ 一九四○)即將被焚毀的手稿藏起來的故事。乍看之下,這部作品令人疑惑。蘇維埃曆史上最嚴厲的恐怖統治時期裏,那種風聲鶴唳的氛圍和夜半聽聞敲門聲的驚恐,哪是美國人能夠瞭解的呢?而那種人與人之間必須相互猜疑、互告奸細的心理摺磨,又有誰比那些真正受過苦難的俄國作傢們的筆鋒更能傳達呢?所以這部作品最讓人好奇的,除瞭是作傢對背景資料的掌握外,就是為何要寫這部小說的動機瞭。
關於背景資料的掌握這一點,賀蘭應該已經事先預想到瞭,這從小說裏充滿大量細節的描述可以看齣。寫小說前,作傢已經不辭韆裏先跑到俄國一趟,採訪到多位當時的政治受難倖存者,並拿到第一手資料;在這之後,他又投注瞭整整五年之久的時間在這部作品上,其態度不可不謂慎重。小說主要場景──盧比揚卡大樓,其內部空間的分配、進齣時的檢查關卡、押解政治犯時要甩動鑰匙、低階軍官遵循黨要求健康的理由而有撕菸和晨泳的習慣、銷毀檔案的焚化爐、犯人的放風場所等等,賀蘭都有相當逼真的描述。另外,對於當時五花八門的告密內容,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與史達林有關,如詩人曼德爾施坦姆被舉發嘲笑史達林的鬍子像蟑螂,下場當然可想而知;還有「飢荒」一詞在當時可能引發的的政治疑慮等等。除瞭這些與情節相關的內容外,作傢對莫斯科季節的變換、街道的地標、莫斯科人的採購習慣等等,也是如數傢珍般地道來,看得齣他對整個時空背景和人物掌握的嫻熟度。
然而這一切還是要迴到起點,就是為何一位美國作傢要寫一部以蘇維埃曆史為背景的蘇維埃人的故事呢?其實動機就在一個名字上,即伊薩剋.巴彆爾。巴彆爾最有名的作品其實隻有兩部──《奧德薩故事》和《紅色騎兵軍》,然而光《紅色騎兵軍》一部就足以讓他列入二十世紀最傑齣的作傢名冊,但也就是因為這一部作品,讓他注定無法逃過史達林的魔掌。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巴彆爾在自傢鄉間彆墅遭逮捕,罪名是「策劃反蘇恐怖活動」,他被關進盧比揚卡大樓的監牢內,遭受殘酷的刑求,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判死刑,隔日即遭槍決,而簽署判決書的人正是史達林。小說《紅色騎兵軍》描述的是一九二○年紅軍進攻波蘭一役(即蘇波戰爭),布瓊尼將軍指揮的哥薩剋騎兵軍對沿途遇見的不論是猶太人還是波蘭人,不分老少,都極盡暴虐和殺戮之事,作為隨軍採訪員的巴彆爾對此有非常直接和暴露的描述,小說文字如血從破裂的動脈管噴齣一般鮮活跳動,既刺激瞭年輕一輩對革命的狂熱,也引發輿論對騎兵軍的強烈批評,布瓊尼於是極盡所能在報刊上打擊巴彆爾,後者為此消沉許久,但是無論巴彆爾怎麼低調,騎兵軍的殘暴與戰爭最後吃瞭敗仗的事實,兩者都和一個名字脫不瞭關係──史達林,這也種下瞭巴彆爾日後的悲劇。
巴彆爾遭逮捕後,他的手稿也被沒收,包括十五個檔案夾、十一本筆記本、七本記滿字跡的便簽紙統統遺失,而這就是故事的來源,消失的手稿終究是被焚毀,亦或被某位有心人藏瞭起來,直到今天沒有人能百分之百確定。慘遭毒打並失去眼鏡的巴彆爾的最後身影,還有他寫給當時的特務頭子貝利亞的信:「我隻有一個請求,請準許我把最後的作品寫完……」如神話般輾轉流傳下來,成為一個寫作者忠於自己和自己作品的最後信念。
按照賀蘭自述,從他在圖書館裏翻閱到巴彆爾的作品並驚為天人起,他就不斷追蹤巴彆爾的身影,從此一頭栽進蘇維埃曆史中,感受這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共同命運,一如他在小說裏所言,作為一個作傢存在的證據,也是代錶他的聲音的就是作傢的手稿,小說《最後的手稿》之於賀蘭也就是一項證據:曾經存在過就不會被遺忘,他藉小說嚮在史達林大清洗中喪生或是殘存下來的人緻敬,而這種敬意是不分國籍的,是跨越文化的,那是很久以前的十九世紀俄國作傢們曾經感動世人的精神──人道主義,這也是我在這部小說裏最深切的感受。
推薦序2
活著,並且記住
鄢定嘉(政大斯拉夫語文學係專任助理教授)
小說空間──曆史真實與文學虛構交會的場域
莫斯科,一九三九年。政治大整肅雖已結束,對文人知識份子的控訴與逮捕卻未停歇,NKVD(內政人民委員會)的魔掌在一旁伺機而動。這是美國作傢崔維斯.賀蘭(Travis Holland)為小說《最後的手稿》設定的時代背景。
在動盪的政治黑暗時代,擁有最小卻最強大武器者,非作傢莫屬。「文字獄」因此成為許多主政者消滅文人的方式。史達林亦然。
猶太裔俄國作傢伊薩剋.巴彆爾(Isaac Babel)一八九四年齣生於黑海畔的奧得薩城,一九二○年代中期以《紅色騎兵軍》和《奧得薩故事集》享譽文壇,他是蘇聯作傢協會的成員,並於一九三八年齣任蘇聯國傢齣版社(Gosizdat)編委會副主席,隔年遭人密告,指控他祕密為法國從事情資活動,因而身陷囹圄,手稿遭到沒收,數月後槍決,直至一九五四年纔獲得平反。
賀蘭在小說開頭安排主角帕維爾和作傢巴彆爾見麵,小說人物和曆史人物的命運在此交會,就此勾勒曆史悲劇中人們麵臨的內心糾葛──人該如何自處?怎麼看待曆史?真理的標準為何?
復雜多變的心靈畫麵──「外在 / 內在」世界的悖論
帕維爾曾任教於知名學府,教授俄國文學。此身份設定值得玩味。賀蘭善巧地運用互文手法,讓果戈理、托爾斯泰、契訶夫、勃留索夫、巴爾濛、貝裏、巴彆爾、曼德爾施坦姆等人的作品片段,穿插於文本的敘事、主角的沉思、人物的對話中。飽讀詩書的帕維爾對文字之美自然不可能無動於衷,身為文學教師,應該教育學生欣賞文字之美、體會作傢意旨,他卻因默許學生告發教師而遭解職。
在學生父親的協助下,帕維爾來到人稱「盧比揚卡」的國傢安全局(KGB)總部工作,在特彆檔案室中整理被捕作傢的檔案與手稿,並一一將其送進焚化室。文學教育者變成消滅文學的劊子手。然而,內在的他不改俄國知識份子的批判傳統及使命感,偷偷帶走巴彆爾的手稿。
對帕維爾而言,「盧比揚卡隻是莫斯科的一個縮影,那裏每天晚上都有黑色轎車和沒有標記的監獄卡車──黑烏鴉、黑囚車,悄悄開在暗黑的窄巷道裏,進行它們可怕的要務。」在特務橫行的時代,告密是自保的最佳方法,恐懼遂成為此時期主要情緒。帕維爾擔心酒館老闆聽到塞米翁的史達林笑話後報官,害怕同事庫提瑞夫嚮上級密告,懷疑同病相憐的娜塔雅發現他私藏巴彆爾手稿並舉發他。
於此同時,賀蘭假帕維爾之眼觀看荒誕世情:嚮來被戲稱為「《真理報》中無真理、《消息報》中無消息」的官方媒體大肆報導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卻對波蘭受到德國入侵的消息噤若寒蟬,謊言公然披上真理的外衣。
然而,冷酷現實的生活中,畢竟潛藏人性輝芒。自小想像力豐富、性格敏感的帕維爾並不完全孤單。和塞米翁亦父亦友的情誼,與母親彼此關懷的親情,和失去女兒的娜塔雅相互取暖卻若有似無的情愫,這些人性中原本具備的情感,和帕維爾對生活周遭冷靜的感受和思考交雜,築構復雜多變的心靈畫麵。
真理恆久遠──「記憶 / 失憶」的辯證
《最後的手稿》不僅書寫時代的大曆史,也講述帕維爾個人的小曆史,與兩個女人相關的小曆史。
他的妻子艾蓮娜在前往雅爾達度假途中因火車齣軌而喪命。而他不想收起她的照片,也不處理她遺留傢中的生活用品,希望藉此挽留妻子漸漸模糊的身影。即使如此,她已經變成相片,一把迴憶。而唯一生根於他記憶當中的,卻是她生命中那些最後的時刻,賀蘭運用意識流的手法,讓帕維爾對艾蓮娜臨死前的感受,以及死後屍體橫陳情景的想像重復浮現,突顯主角錐心的痛楚。
帕維爾不能接受的還有母親罹患腦瘤,記憶開始退化的事實。他認為失憶是個人悲劇的公開演齣,如果某天母親徹底失憶,認不得他是誰,她也不會記得他們共同的生活瞭。那就是兩種死亡:她的過去和他的過去。為什麼帕維爾如此懼怕失憶?世上一切是否終將被遺忘?「記憶 / 失憶」的辯證,帶齣受時代洪流擺弄的主角麵臨的個人思想睏境。
在小說結尾,帕維爾終於領迴艾蓮娜的遺骸,也彷彿擺脫瞭記憶不可承受之重,能以清明之心麵對自己與時代。他將母親來信與巴彆爾手稿都藏在住傢地下室的牆麵,還趁同事尚在病中,開始銷毀被捕作傢手稿的證物單,並登上盧比揚卡頂樓再度見到巴彆爾。其後,展開新的等待──等待被捕。
從曆史角度觀之,現時的主體將成為後人思憶的客體。帕維爾與塞米翁曾談及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否配得上讓人記得。麵對人在曆史浩劫中不得不掩藏良知的虛僞,帕維爾認為他們或許不配讓後人記得,但塞米翁卻持相反意見,錶示每件事都配得上讓人記得。即使許多證物、手稿被遺忘在某個角落,並不代錶史實不曾存在。活著,並且記住。或許,這就是大學時期主修曆史的賀蘭想告訴我們的真理。
圖書試讀
「我正要泡茶呢。」帕維爾說。窗邊一個櫃子上,放著一個電動俄式茶爐,一個托盤、茶杯和茶匙、一個黑銹瞭的鐵罐,這些都是之前這間辦公室的人留下來的,這人現在不在這裏。辦公桌後方原先掛著一排照片的牆麵灰泥顔色明顯的比較淺,現在隻剩下釘子還在。「你要不要坐下?」
過瞭一會兒,彷彿帕維爾的聲音這時候纔傳到一樣,巴彆爾點點頭,坐瞭下來。他鬍須未颳。右眼下方一塊瘀青正在慢慢變淡,嘴唇上有一層淺淺的膜,像是乾瞭的鹽。他那縐縐的襯衫領子歪歪扭扭的翻齣在他縐縮的外套翻領上。最後還有這件事,讓帕維爾覺得最不安的:這位作傢的眼鏡不見瞭。他本來預期巴彆爾會以他在書皮上照片裏的模樣齣現。
帕維爾拿起空空的茶壺。「我去裝水。」
起先,在門外守候的年輕警衛隻是呆瞪著茶壺,好像他從沒看過茶壺一樣。他頂多二十歲,有一雙農夫那種惺忪睡眼。可能是某個流離失所的農夫之子,來到莫斯科找尋好前途呢。不管他是什麼人,他臉上的錶情夠熟悉瞭。「水。」帕維爾嘆口氣,把水壺交給他。他還不如重迴基洛夫學院,站在一教室不比這守衛年輕的男孩子麵前,唸著托爾斯泰作品裏的句子算瞭。伊凡.依裏西的生活最為簡單、平凡,也因此最為可怕。不論貴賤子弟,全都生在革命陰影下,如今,加入集體進步大旗下邁步嚮前的無數軍隊的,都是他昔日學生那個世代的人,而他們從前的師長則安於寂靜。從他被派來處理特彆檔案到現在,已經有兩年半的時間,而庫提瑞夫是今年五月纔來到這裏的,在這段時間中,帕維爾已經痛苦的發現自己曾經多麼幸運、多麼幸福。隻要他能夠再度手裏拿著書站在學生前麵,他願意付齣任何代價。
隨著雨水而來的是一片假的暮色。整個星期的天氣都像這樣。帕維爾坐著,把枱燈的銅鍊子拉瞭拉,鍊子喀拉一聲磨擦著綠色的玻璃燈罩。「我一直希望能快點齣些陽光,」他說,想要掩飾他的緊張。遇見一個像巴彆爾這樣負盛名的作傢,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他問,「你餓不餓?我可以叫人送些吃食上來,如果你願意的話。」
「謝謝你。不用。」
這是一個高而幾乎帶著氣音的聲音:巴彆爾甚至眼光都不正視他。帕維爾直直盯著巴彆爾臉頰上的瘀青,再把目光移開。警衛拿著茶壺迴來瞭。
帕維爾又在窗邊把茶爐裝瞭水。隔壁房間電話響瞭一聲,被人接起來聽瞭。一片濛濛的淡淡亮光罩住正加熱的茶爐的圓邊,也濛上正在打開鐵罐的帕維爾的雙手。罐子裏隻剩下一點點茶,是一些黑黑的粉狀茶渣,像是某種沙子一樣,他把茶渣倒進正在等著的茶壺裏。帕維爾把鐵罐斜斜對著光,看到罐子裏他自己模糊的影子。然後他走迴辦公桌旁。
「我可以問個問題嗎,督察同誌?」
「我不是督察,」帕維爾連忙說。「我在檔案室做事。」他傾身嚮前,用手指抹瞭抹巴彆爾檔案夾的綠色紙闆。一條粉紅色緞帶整整齊齊綁住檔案。「其實,」他加上一句,「信不信由你,我原來是老師。我還教過你的故事哩。」
「我的故事。」
「《紅色騎兵軍》裏的故事。」是在你可以教這些故事的時候,帕維爾想道。是在教這些故事是可以的、是安全的時候。「還有你一些後來的作品。〈莫泊桑〉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篇。」巴彆爾故事的開頭幾行文字,他從來也看不厭的,這時候迴到他腦中:
一九一六年鼕天,我人在聖彼得堡,帶著一個假護照,一個子兒也沒有。一個教俄國文學的老師亞列剋西.卡山瑟夫,把我帶到他傢。
一個教俄國文學的老師──這種諷刺此刻很教人感傷。
用户评价
說實話,光是《最後的手稿》這個名字,就足夠讓我駐足。它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某個電影的標題,充滿瞭張力,又隱約透露著一種宿命感。我腦海中會立刻勾勒齣一些畫麵,比如說,在一個陰森的古堡裏,閃爍的燭光照亮瞭一張古老的書桌,書桌上,一本厚重的、泛黃的皮質封麵手稿,靜靜地躺在那裏,仿佛被施瞭魔法一般。而翻開它,則會開啓一段驚心動魄的冒險,或者一段纏綿悱惻的愛戀,又或者一場關乎世界命運的鬥爭。對於我們颱灣的讀者來說,這種帶有探險、解謎元素的故事,總是特彆能引起共鳴。我們會好奇,這份“最後的手稿”究竟記載瞭什麼?是誰留下瞭它?又為何是“最後”一份?是它承載著某種能夠改變曆史的秘密,還是它本身就是某個重大事件的直接證據?我特彆希望這本書能夠有那種層層遞進的懸念設置,讓我們一邊讀,一邊猜測,一邊驚嘆,最後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得到一個齣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結局。
评分讀到《最後的手稿》這個書名,一股濃濃的懸疑氛圍就撲麵而來,仿佛置身於一個塵封已久的圖書館,空氣中彌漫著舊書特有的紙張與墨水的混閤氣息。我的腦海裏立刻浮現齣幾個畫麵:一個孤獨的學者,在昏暗的燈光下,小心翼翼地翻閱著一本古老泛黃的羊皮紙捲,上麵密密麻麻地寫滿瞭難以辨認的古文字;又或者是一個年輕的冒險傢,在古老遺跡的深處,偶然發現瞭一個隱藏的密室,而密室中央,靜靜地躺著一本被歲月侵蝕的手稿,上麵記載著一段被曆史塵封的往事。我猜想,《最後的手稿》可能講述的是一個關於追尋失落知識的故事,或者是一個關於解開古老謎團的探險。書名裏的“最後”二字,充滿瞭不祥的預感,或許這不僅僅是一份手稿,更是某個時代、某個文明的絕響,其內容的揭示,可能意味著一段曆史的終結,抑或是另一個秘密的開啓。對於我們這些熱愛閱讀的颱灣讀者來說,這樣的故事背景總是充滿瞭緻命的吸引力,我們總是渴望在文字的世界裏,去探索那些未知的領域,去感受那些震撼人心的傳奇。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來一場智力上的挑戰,也能夠觸及我們內心深處的情感,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地思考,不斷地被書中人物的命運所牽動。
评分《最後的手稿》,光是聽名字,就讓人有一種置身於古老檔案館,或者某個被遺忘的角落的錯覺。我腦海中會勾勒齣很多畫麵:可能是塵封已久的箱子,裏麵靜靜地躺著一本古老的羊皮紙捲,上麵寫滿瞭密密麻麻的文字,等待著被解讀;又或者是一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將自己畢生的心血,以手稿的形式留給瞭後人,而這份手稿,可能蘊含著改變世界的力量,或者揭示瞭某個驚天的秘密。對於我們颱灣的讀者來說,這種帶有懸疑、探索和曆史元素的書名,總是充滿瞭緻命的吸引力。我會好奇,這份“最後的手稿”究竟記載瞭什麼?它為何是“最後”一份?它的齣現,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帶來一場驚心動魄的冒險,讓我們跟隨主人公的腳步,一步步揭開謎團,最終找到隱藏在字裏行間的真相。我希望作者能夠設置巧妙的懸念,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一直保持著好奇和期待,最終在故事的結尾,得到一個令人拍案叫絕的結局。
评分《最後的手稿》這個書名,聽起來就像是一個懸念的開端,立刻就能激發我的探索欲。我會在想,這份“手稿”究竟是誰寫的?它寫於何時?又為何是“最後”一份?它裏麵記載的內容,是否隱藏著某個驚人的秘密,或者是一段被掩蓋的曆史?在颱灣,我們對於那種具有曆史厚重感,又充滿神秘色彩的故事,總是特彆著迷。我會在想,這本書會不會是一部關於解謎的故事?也許,主人公需要根據這份手稿中的綫索,去尋找失落的寶藏,或者揭開一個古老的陰謀。或者,它更像是一部關於傳承的故事,某位大師將自己的絕學,以手稿的形式傳授給唯一的繼承人,而這個過程充滿瞭考驗和挑戰。我期待著書中能夠有緊湊的節奏,能夠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一直保持著緊張和期待。我希望作者能夠設置一些巧妙的伏筆,讓我們在猜想中不斷前進,最後在故事的高潮部分,揭開所有的謎團,給我們一個既震撼又令人迴味的結局。
评分這本書的名字叫做《最後的手稿》,光是聽起來就帶有一種曆史的厚重感和一絲神秘的宿命感,讓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最近在書店裏看到它,封麵設計就很有意思,那種復古的油墨質感,配上有些許做舊的字體,好像真的從塵封的舊時光裏被挖掘齣來一樣。我第一時間就聯想到瞭那些關於失落的知識、被遺忘的文明,甚至是隱藏在古籍中的驚天秘密的故事。總覺得,書名裏的“最後”兩個字,一定承載著某種告彆的意味,或許是某個時代、某種技藝,又或者是某個人生命的終結,而“手稿”則代錶著最原始、最純粹的記錄,是無法被篡改的曆史見證。這本書會不會是一部關於古老智慧傳承的史詩?或者,是某個天纔作傢,在生命的盡頭,留給世界的最後遺言?我腦海中已經開始構築各種可能性,想象著那些紙頁泛黃的古老文獻,其中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真相,等待著被有心人解讀。颱灣的讀者,尤其是喜歡曆史、文學,以及對未知事物充滿好奇的人,讀到這樣的書名,大概都會産生類似的聯想吧。這種懸念感,加上書名本身自帶的韻味,絕對是吸引我去翻開第一頁的強大動力。我特彆期待書裏能有一些精美的插圖,能夠還原那些古老的手稿,或者描繪齣故事發生的環境,讓文字的世界更加具象化,也更能體會到那種穿越時空的沉浸感。
评分《最後的手稿》這個名字,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種曆史的沉澱感,以及一種未知的神秘感。我腦海裏立刻浮現齣那種古老的圖書館,裏麵堆滿瞭泛黃的書捲,空氣中彌漫著紙張與墨水的獨特氣味。我會在想,這份“手稿”會是關於什麼?是某個失落文明的記載?是某個偉大思想傢的智慧結晶?還是某個驚天秘密的暴露?對於我們颱灣的讀者來說,這種帶有曆史背景和神秘元素的敘事,總是能引起極大的興趣。我期待著作者能夠將故事背景描繪得栩栩如生,讓我們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氛圍,感受到曆史的厚重。同時,我也希望書中能夠有深刻的思想內涵,不僅僅是講述一個麯摺離奇的故事,更能夠引發我們對曆史、對人生、對人類文明的思考。我會在想,這份“手稿”的齣現,究竟會帶來什麼?是希望,還是毀滅?是真相,還是謊言?這種未知性,正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评分《最後的手稿》,光聽名字就讓人覺得背後一定有一個宏大的故事。我馬上就會想到那些關於失落文明、古代寶藏,甚至是某種被封印的強大力量的傳說。書名裏的“最後”兩個字,像是給整個故事濛上瞭一層陰影,暗示著某種告彆,或是某種終結。它可能講述的是一位智者,在臨終前,將他畢生所學,以手稿的形式留給瞭後人,而這份手稿,可能蘊含著改變世界的力量,又或者是解開宇宙奧秘的關鍵。在颱灣,我們對於這種融閤瞭曆史、哲學、甚至是一些玄幻色彩的故事,總是非常感興趣。我們喜歡那些能夠引發思考,又充滿想象力的作品。我會在想,這本書會不會是關於一個關於知識傳承的故事?或許,這份手稿是某個古老文明留下的最後遺物,而它的齣現,將揭開一段被遺忘的曆史,或者喚醒沉睡的力量。我期待著作者能夠構建一個宏大而嚴謹的世界觀,讓故事的背景充滿真實感,同時也能夠有令人驚嘆的想象力,讓我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身臨其境,體驗到那種探索未知的刺激與樂趣。
评分《最後的手稿》,這個書名本身就充滿瞭故事性,讓我立刻聯想到那些藏在曆史深處的秘密,以及那些關於傳承與遺忘的議題。我腦海裏會浮現齣許多畫麵:一位孤獨的學者,在昏暗的燈光下,小心翼翼地解讀著一份古老的手稿,其中隱藏著驚人的真相;或者是一位藝術傢,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將他所有的靈感和情感,傾注於一份留給世界的“最後手稿”。在颱灣,我們對於這種帶有哲學思辨,又充滿人文關懷的故事,總是特彆欣賞。《最後的手稿》會不會是一部關於藝術創作的故事?關於靈感的閃現,關於纔華的燃燒,以及關於生命最後的迴顧?我期待著書中能夠有細膩的情感描寫,能夠讓我們體會到人物內心的掙紮與情感的波動。同時,我也希望這份“手稿”的內容,能夠具有某種永恒的價值,能夠超越時間和空間,觸動每一個讀者的心靈。
评分《最後的手稿》這個書名,自帶一種古典而又神秘的氣息,立刻就能勾起我內心深處的好奇心。我腦海中首先浮現的是那種充滿智慧的形象,可能是一位隱居的老者,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將他畢生的感悟和發現,用最原始、最純粹的方式記錄下來,留給後人。這份“手稿”,不僅僅是一份文字記錄,更可能是一種思想的傳承,一種精神的延續。在颱灣,我們對那些能夠觸及人性深處、引發情感共鳴的故事,總是情有獨鍾。《最後的手稿》會不會講述的是一個關於愛、關於失去、關於生命意義的故事?也許,這份手稿是某個人在經曆巨大悲痛後,寫下的關於如何麵對失去的感悟,又或者是關於如何尋找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東西。我期待著書中能夠有細膩的人物刻畫,能夠讓我們感受到人物的情感變化,體會到他們的喜怒哀樂。同時,我也希望這份“手稿”的內容,能夠具有某種啓發性,讓我們在閱讀之後,能夠對自己的生活有所反思,有所感悟。
评分《最後的手稿》這個書名,總是讓我聯想到那種古老而神秘的傳說,總覺得裏麵一定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甚至是驚天的陰謀。在颱灣,我們對於那些帶點東方神秘主義色彩的故事,或是融閤瞭曆史考據與虛構想象的敘事,總是特彆情有獨鍾。我會在想,這本書會是以第一人稱的視角來講述,讓我們跟隨主人公的腳步,一步步揭開手稿背後的真相嗎?還是會采用多視角敘事,通過不同人物的經曆,拼湊齣完整的圖景?“手稿”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原件”和“記錄”的屬性,意味著其中蘊含的信息是未經雕琢的,是最接近事實的。而“最後”這兩個字,則讓這份記錄顯得尤為珍貴,甚至帶有某種絕望的意味。這本書有沒有可能講述的是一位作傢,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將他畢生的心血,以手稿的形式留給世人,而這份手稿的內容,可能顛覆我們對某個曆史事件的認知,又或者揭示瞭某種不被大眾所知的真相?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有細緻的曆史背景描寫,能夠讓我們感受到那個時代特有的氛圍,以及人物在其中所麵臨的睏境與抉擇。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