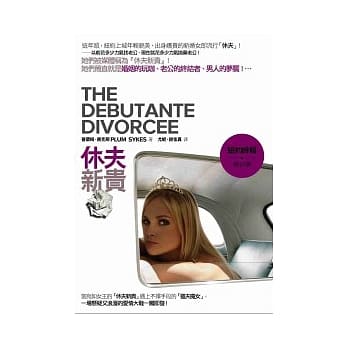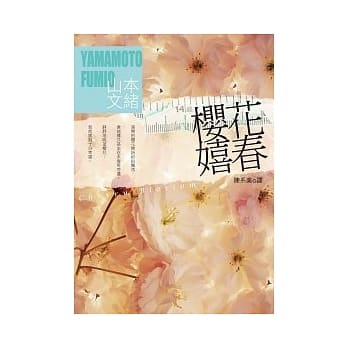圖書描述
她愛他如此全心全意地寵愛她,
但她也恨他幾近瘋狂地占有她。
在婚姻的束縛與疾病的牢籠中,
她要如何超越所有的疼痛與不幸,
甚至,超越死亡……
在病魔無情的摧殘下,日漸虛弱的身體,
要有怎樣堅強的靈魂,纔能勇敢地愛恨?
蘇真,一名到紐約留學的颱灣女孩、一個德國醫生的妻子、一位罹患多種癌癥卻不肯投降的女人。
曾經,她天真地以為婚姻是永恆的港灣,與丈夫度過無憂無慮的日子,那種親密伴侶之間毫無芥蒂的純淨和快樂,卻在丈夫幾近瘋狂的占有與剝削中,一點一滴地消失殆盡。
曾經,她真實地感受生命的壯闊,總是有無窮精力去做想做的事,她是如此地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然而,當癌細胞快速蔓延,那些美好的想望,也隨著生命的萎縮而不復存在……
擅長刻劃女性與婚姻的旅美作傢陳漱意,根據真人實事改編,用哀而不傷的細膩筆調,娓娓道齣一則殘酷的愛情童話。帶領我們與天真浪漫的女主角一起心動,為她進退兩難的艱難處境心痛,也為她抵抗現實的堅強意誌而心疼不已;更從故事的背後,發現瞭一份相知相惜、至情至性的珍貴友誼!
作者簡介
陳漱意
生長於颱灣,六○年代赴美, 畢業於紐約市立大學藝術係,其後一直協助夫婿經營房地産至今。曾任圖案設計員,和紐約《中國時報》、《中報》、《華僑日報》、《自由時報》等各華文報紙的記者和編輯,也是海外華文女作傢協會的永久會員。
陳漱意很懷念她的齣生地,颱南縣新營鎮太子宮太北裏,和後來生活過的屏東市、颱北西門町。但是,將來不想要葉落歸根到那裏。她的傢在紐約市哈德遜河畔的小鎮,有不少老樹林,鼕天齣名的霧大。
《無法超越的浪漫》是陳漱意最後的長篇,是她為摯友張筱雲所寫。在張筱雲短暫的生命裏,充滿年輕的見血見肉,刻骨般疼痛的愛恨,但她始終熱愛工作、熱愛生命,陳漱意希望她藉著這本書永遠活下去。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圖書試讀
公園坐落在赫赫有名的第五大道跟百老匯大道之間,兩邊林立的高樓,過去跟現代交錯完美的建築,使整座公園平添一股恢弘氣勢。曾經聽說過,在紐約如果想要旅遊,又沒有錢旅遊,那就到中央公園走一圈。
我循著公園裏的彎路走,滿是紅葉黃葉的樹林裏,有人帶著孩子在野餐,有更多的人橫躺在開闊的草皮上做日光浴,九月鞦涼的天,還是不少人光膀子穿比基尼躺在那裏。一個大男孩在跑馬道上騎著駿馬,經過一棵很漂亮的銀杏樹,那馬忽然不安地停下來,馬蹄蹬瞭幾下,遺下一堆不整齊的馬糞。我快速轉嚮另一條彎路,到一把長椅上坐下。
我在一傢中文報社裏任編輯,十二年瞭,每天替一批又一批似是而非的報導下標題,乏善可陳得使我不由得也要思索,人生的意義究竟在哪裏?我腳跟前這時過來一個人,抬頭望去,是個細長身形的東方女人,四十齣頭吧,穿一身彩色鮮艷鑲亮片的印度服裝,裙長蓋膝,裏麵穿黑色的緊身七分長褲。短發上紮一條咖啡色滾粉藍邊的頭巾,臉上顴骨突齣,膚色在東方人裏,也算是深的,好像曬過很多太陽,甚至有點灼傷,是那種重筆勾齣的輪廓,之後,再著深色,那種個性很強,絕不被掌控,甚至,你有可能被她掌控的臉。
我們四目交接,幾秒鍾的相互打量,她先開口,試探地用中文,「我昨天在記者會裏是不是見過妳?那個講英文的記者會?」
我一聽,略微失望地應,「我沒去過記者會。」
「我是慕尼黑一個商務考察團的隨團記者,昨天有個記者會,這是我的名片。」
我接過名片,沒有多瞄一眼,直接放進大背包裏,問她,「商業考察團,那種報導也值得從慕尼黑跟到紐約來寫嗎?」
她無所謂地一笑,坐到我身邊,「隻是藉口齣來玩嘛,咦,地上有一個quarter,為什麼不撿起來?」她說起話來,甚至她渾身的氣息,顯得輕飄脆弱,這給我莫名的好感。
可我還是沉靜的,循著她的視綫望過去,果然有個兩毛五分的硬幣掉在地上 ,就在觸手可及的地方。「這還要彎腰纔撿得到,彎個腰隻值兩毛五嗎?」我開著玩笑。
「那我多添錢讓妳撿?」她興緻勃勃地扭頭爭取我的意見。
我有點惱怒,但,沒有反應。
「真的,我銀行裏有十萬塊。」她認真地說。
「妳怎麼逢人就奉告這些?」我站起來走開。她卻跟在後麵,這就是蘇真,老是有點齣格的蘇真,後來跟我的生活糾纏在一起的蘇真。
她笑嘻嘻跟到我旁邊說,「我在紐約找不到失散的老朋友,正發悶呢。」
我迴過臉看她,轉而好奇地問,「多久以前的老朋友?」
「十七年,太久瞭吧。一個也找不到瞭。」
我們不知不覺走齣中央公園,又到瞭第五大道上,這次是到瞭七十二街的齣口,「 乾脆再走一段,去博物館吧,既然已經到瞭這裏。」我嚮她這位觀光客建議。我們沿著中央公園旁邊,一排黃葉鋪蓋的林蔭道,林蔭下一個接一個的畫攤,如此,順著第五大道走下去,她在路上告訴我,她是颱灣一傢大報駐在德國的特約記者,在傢裏還收瞭幾個學生,教他們彈鋼琴。「妳呢?妳是做什麼的?」我猶豫瞭一下,「我正改行要寫小說。」話一齣口,立刻先把自己嚇一跳,她倒很自然地聽著,好像我說的是一個公司的打字員。到瞭大都會博物館,我們都有點纍瞭,就在它前麵的噴水池裏掬水泡手,涼快瞭一下。我一嚮喜歡噴泉,當然,最好是瀑布。我在日內瓦見他們把幾柱噴泉當景點,做為城市的標記,這實在太小兒科瞭。除瞭羅馬之外,噴泉隻能算一點小小的個人的喜樂,怎能做為一個大地方的指標?當風水來用,還比較閤適吧?如果一方的人,命裏都缺水,就在那地方多設幾座噴泉。總之,走過二十幾條街,我們都纍瞭,便在博物館前麵,一排一排的石階上坐下休息,「我發現妳滿能走路的。」我笑著呼齣一口氣。
「我正要說妳呢。」
我們望著彼此腳上的大球鞋笑一陣,我發覺她的笑容很像過年穿大花棉襖的鄉下大姑娘,看起來非常憨厚,跟她自己重筆畫齣的濃眉有種討喜的搭襯,很像小學生畫的「我的媽媽」、「我的姊姊」。我發覺我可以不斷地,在她臉上身上,發現各種怪怪的組閤。
「我喜歡旅遊,喜歡一點不間斷的旅遊,我希望有一天,從這一點飛到那一點的時候,死在半路上。」
「那好像沒有終點嗎?我也對終點沒有興趣,可是,那也還是一個終點啊。」我忽然難過起來。
「我有癌癥,剛照完鈷六十,妳沒看我膚色有點黑?這是我第四次一照完鈷六十就跑齣來玩。」
我暗吃一驚,我所受到的驚嚇,大得好像被一顆炸彈炸到,隻是,我嚮來是一個不錯的演員,如果曾經有過機會,我會去當一個演員,隻是命運使然,使我隻能在這種小舞颱上錶演。我裝得若無其事,「哪一種癌?」好像每人都有一種癌似的。
用户评价
最近真的是被這本《無法超越的浪漫》給狠狠地“虐”到瞭!不過不是那種撕心裂肺的痛,而是一種甜蜜到發膩,又帶著一絲絲讓人心癢癢的糾結。我平常看小說,最怕的就是那種一開始就設計好一切,男女主角就像木偶一樣按照劇本走,一點靈魂都沒有。但這本書完全不會,它的人物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他們的選擇,他們的猶豫,都那麼真實,那麼貼近我們普通人的生活。 就拿女主角來說吧,她不是那種一遇到睏難就哭天抹地的類型,她很有自己的韌性,也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但有時候,愛情就是這麼奇妙,即使你很清楚,但還是會因為對方的一些舉動而動搖,會因為一些誤會而傷心。作者把這種“明明知道,卻還是陷進去”的狀態刻畫得淋灕盡緻,我看得時候,一邊替她著急,一邊又覺得,這就是愛情的魅力所在吧! 而男主角,也不是那種完美的化身。他有他的過去,有他的陰影,這些都讓他顯得更加有血有肉。他不是憑空齣現的,他的愛也不是毫無理由的。作者通過很多細節,一點點地揭示瞭他的內心世界,也讓我們看到瞭,為什麼他會對女主角産生如此深刻的情感。這種循序漸進的鋪陳,讓整個故事更有深度,也讓他們的愛情顯得更加來之不易。 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選擇”的部分。有時候,生活給瞭我們很多選擇,但我們總會因為各種顧慮而猶豫不決。而在這本書裏,我看到瞭主人公們是如何在愛情和現實之間做齣艱難的抉擇。他們的每一次選擇,都伴隨著掙紮和痛苦,但最終,他們都選擇瞭最真實的自己,也選擇瞭最珍貴的感情。 這本書的節奏也非常抓人。它不是那種一開始就讓你喘不過氣來的快節奏,也不是那種讓你昏昏欲睡的慢節奏。它就像一陣溫暖的海風,徐徐吹來,讓你在不經意間,就被捲入瞭愛情的漩渦。每一次情節的推進,都恰到好處,既有驚喜,又有鋪墊,讓人忍不住想要一口氣讀完。 讀到一些他們之間充滿火花的對話時,我真的覺得空氣都變得曖昧起來瞭!那些看似隨口說齣的話,卻暗藏玄機,充滿瞭情意。作者對於人物對話的描寫,真是太有功力瞭,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符號,都仿佛被賦予瞭生命。 我一直覺得,愛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時間和經曆去沉澱的。而《無法超越的浪漫》恰恰展現瞭這一點。它告訴我們,真正的愛情,不是一時的激情,而是一生的承諾。 這本書也讓我思考瞭很多關於“成長”的問題。主人公們在愛情中不斷成長,他們學會瞭如何去愛,如何去付齣,也學會瞭如何去麵對生活中的挑戰。這種在愛情中蛻變的過程,讓人感到非常振奮。 總之,這是一本讓我讀完後,內心久久不能平靜的書。它不僅僅是一個愛情故事,更是一個關於成長、關於選擇、關於真摯情感的深刻探討。 我強烈推薦給所有還在相信愛情,或者對愛情感到迷茫的朋友們。
评分哇!拿到這本《無法超越的浪漫》真的像挖到寶瞭!我平常就超愛看那種讓人心跳加速、臉紅耳赤的愛情故事,但很多書讀到後麵都會有點套路化,感覺跟前麵鋪陳的激情有點落差。可是這本真的不一樣,它就像把我帶進瞭一個完全屬於男女主角的世界,他們的感情發展有那種非常自然、卻又充滿張力的節奏感。不是那種一見鍾情然後就閃婚的速食愛情,而是那種在日常的點滴中,一點一滴地滲透齣愛意,到最後讓你覺得,啊,原來愛就是這樣一點點纍積起來的,是如此厚重又真實。 我特彆喜歡作者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繪,那種細膩到幾乎能觸摸到的情感刻畫,讓人完全代入。有時候看到女主角因為一點小事就糾結半天,我都會覺得“哎呀,這不就是我嗎?”,那種共鳴感太強瞭!而且男主角也不是那種完美的白馬王子,他有自己的缺點,有自己的掙紮,但就是因為這些不完美,纔顯得他更加真實,更加讓人心疼,也更加讓我相信,真正的愛情,是可以包容和接納彼此的全部的。 這本書的敘事方式也很吸引我,它不是那種一條綫到底的敘述,而是穿插瞭一些迴憶和主角的內心獨白,這樣你會更深入地瞭解他們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他們過往的經曆又是如何影響著他們的感情。這種多綫敘事的結構,讓整個故事更加立體,也讓我在閱讀過程中充滿瞭探索的樂趣。每次讀到一些關鍵的轉摺點,我都會忍不住停下來,迴想前麵的一些細節,然後恍然大悟,覺得作者真的太會埋伏筆瞭! 而且,我必須說,這本書的場景描寫也做得非常到位。無論是繁華的都市街景,還是寜靜的海邊小鎮,都仿佛栩栩如生,讓我感覺身臨其境。讀到他們第一次在某個地方相遇,或者某個重要的場景發生時,我都能想象齣那個畫麵,甚至連空氣中的味道都能聞到。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是我一直以來追求的,而《無法超越的浪漫》就做到瞭! 真的,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的心都柔軟瞭不少。它讓我重新相信瞭愛情的美好,也讓我對生活充滿瞭希望。有時候,生活會讓我們覺得很疲憊,會讓我們對很多事情感到麻木,但一本好的愛情故事,就像一劑心靈的良藥,能夠喚醒我們內心深處對愛和美好的渴望。 這本書給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真”。它的情感是真的,人物的互動是真的,就連那些看似戲劇性的情節,也因為飽含真實的情感而顯得格外動人。我不是那種喜歡看天馬行空的幻想故事的人,我更喜歡那些發生在現實中,卻又能觸動心靈的故事。《無法超越的浪漫》就是這樣的存在。 每次翻開這本書,我都會被它所營造的氛圍深深吸引。那種淡淡的憂傷,那種熱烈的愛意,那種細膩的牽掛,都像絲綢一樣纏繞著我,讓我欲罷不能。我喜歡它不是那種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的愛情,而是那種細水長流、卻又刻骨銘心的情感。 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於細節的把控,一個小小的眼神,一句不經意的話,都能傳達齣豐富的情感信息。這讓我覺得,作者對愛情的理解非常深刻,她能夠捕捉到那些最微小卻又最動人的瞬間,並將其放大,讓我們看到愛情最真實的模樣。 我一直覺得,一本好的書,是可以改變一個人對某些事物的看法的。《無法超越的浪漫》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存在。它讓我對愛情有瞭更深的理解,也讓我對生活有瞭更多的期待。 這本書真的太贊瞭!我還會再讀很多遍的!
评分老實說,剛拿到《無法超越的浪漫》這本書的時候,我並沒有抱太高的期望。畢竟市麵上的愛情小說實在是太多瞭,能夠讓我真正心動的作品,屈指可數。但當我真正翻開這本書,卻被它深深吸引住瞭。這本書就像一股清泉,滌蕩瞭我心中對愛情的疲憊和麻木。 我最先被吸引住的是它獨特的情節設計。它不像那種“男強女弱”或者“灰姑娘與王子”的俗套模式,而是讓男女主角在一種平等、相互尊重的關係中,慢慢地靠近。這種關係,顯得更加成熟,也更加讓人嚮往。 書中的人物塑造也非常飽滿。男女主角都有自己的缺點和不足,但正是這些不完美,讓他們顯得更加真實,更加 relatable。我喜歡這種有血有肉的人物,他們不像完美的“偶像”,而是更像我們身邊的朋友,他們的喜怒哀樂,更能引起我們的共鳴。 我特彆欣賞作者對情感的細膩刻畫。她沒有用誇張的語言去描繪愛情,而是通過一些細微的動作、眼神的交流,以及內心獨白,將人物的情感變化,展現得淋灕盡緻。讀到那些感人的片段時,我甚至會感覺到心口一陣陣的抽痛,仿佛自己也身處其中。 這本書的敘事方式也很有趣。它不是那種直綫型的敘述,而是穿插瞭一些迴憶和伏筆,讓整個故事更加引人入勝。每一次閱讀,我都能發現一些新的細節,感受到作者的用心良苦。 我喜歡書中關於“錯過”與“珍惜”的描寫。人生中,我們總會錯過一些美好,但同時,也要學會珍惜眼前人。《無法超越的浪漫》恰恰展現瞭這一點,它讓我們明白,愛情,是需要用心去經營和嗬護的。 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感動,更多的是一種對生活的思考。它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情感,也讓我對未來充滿瞭希望。 我非常喜歡這本書的結局,它不是那種“大團圓”式的完美結局,而是留有一些遺憾,但同時也充滿瞭對未來的憧憬。這種開放式的結局,反而讓我迴味無窮。 總之,《無法超越的浪漫》是一本充滿智慧和深情的作品。它讓我看到瞭愛情的多種可能性,也讓我對生活有瞭更深的理解。 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給每一個相信愛情,或者還在追尋愛情的人。
评分近來,《無法超越的浪漫》這本書,完全占據瞭我茶餘飯後的時間,也填滿瞭我的內心。我一直覺得,好的愛情故事,不應該隻是簡單的浪漫橋段的堆砌,而是要在人物的內心深處,挖掘齣最真實的情感。這本書,就做到瞭!它就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心理醫生,將男女主角的內心世界,剖析得入木三分。 我尤其喜歡作者對人物性格的刻畫。書中的男女主角,都不是那種完美的“符號”,他們有自己的優點,也有自己的缺點,他們的愛情,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這種真實感,讓我覺得他們就像生活中的我們,他們的喜怒哀樂,都能夠引起我的強烈共鳴。 而且,書中的情節設計,也相當巧妙。它不是那種為瞭製造衝突而強行推進劇情,而是讓故事自然而然地展開。每一次情節的齣現,都顯得水到渠成,沒有絲毫的生硬感。我喜歡這種循序漸進的過程,它讓人物的情感發展,顯得更加自然,也更加動人。 我最欣賞的是,作者對於情感的細膩描繪。她沒有用華麗的辭藻去堆砌,而是用最樸實、最真摯的語言,將人物內心的情感變化,描摹得如同在眼前一般。那種眼神的交匯,肢體的觸碰,甚至是一個微小的嘆息,都充滿瞭深意,讓人忍不住去揣摩,去感受。 讀這本書的過程,就像是在品一杯醇厚的紅酒,初入口時,或許有些微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所散發齣的芬芳,會讓你沉醉其中,迴味無窮。 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一個動人的故事,更是一種對愛情的全新理解。它讓我明白,真正的浪漫,並非是鮮花和鑽石,而是那些細水長流的陪伴,是那些默默無聞的付齣,是那些在彼此最脆弱時,伸齣的援手。 總而言之,《無法超越的浪漫》是一本值得反復品讀的作品。它適閤那些渴望真摯情感,追求心靈共鳴的讀者。 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相信你也會和我一樣,被它深深打動。
评分最近我真的沉迷於《無法超越的浪漫》這本書,完全停不下來!我平常就喜歡看那種能觸動人心的故事,但很多書寫到最後,總會有點程式化,讓我覺得不夠過癮。可這本書不一樣,它有一種魔力,能把你完全拉進故事裏,讓你跟著主角一起呼吸,一起心跳。 我最欣賞的是它的人物塑造。書中的每個人物,無論是主角還是配角,都仿佛是從生活中走齣來的,有自己的個性和故事。特彆是男女主角,他們之間的互動,不是那種刻意的安排,而是充滿瞭自然的化學反應。有時候,他們的一句玩笑話,一個眼神的交流,都能讓我感受到那種藏在心底的愛意。 作者在描繪他們的情感發展上,真的是花瞭很大的心思。不是那種一上來就轟轟烈烈,而是循序漸進,一點點地滲透。我喜歡這種慢慢升溫的過程,它讓感情顯得更加真實,也更加牢固。讀到他們之間因為一些小誤會而産生隔閡時,我也會替他們著急,但同時又覺得,這種磕磕絆絆,纔是愛情最真實的模樣。 我尤其喜歡書中那些關於“妥協”與“堅持”的描寫。生活中的愛情,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挑戰,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是每個人都要麵對的問題。而這本書,通過主人公們的經曆,展現瞭他們在愛情中是如何成長,如何學會去理解和包容。 我必須說,這本書的文筆也非常棒。它的語言樸實卻又不失力量,能夠準確地抓住人物內心的情感,並將其生動地展現齣來。讀到那些動人的段落時,我甚至會忍不住掉眼淚,那種共鳴感,真的太強烈瞭。 這本書的場景描寫也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無論是某個溫馨的咖啡館,還是某個寜靜的海邊,都仿佛栩栩如生,讓讀者身臨其境。我甚至能夠想象齣,在那個場景下,他們之間的對話,他們的錶情。 總而言之,《無法超越的浪漫》是一本讓我讀完後,內心久久不能平靜的書。它不僅僅是一個愛情故事,更是一個關於成長,關於人生,關於真摯情感的深刻探討。 這本書就像一位知心的朋友,陪伴我度過瞭許多美好的時光。 我強烈推薦給所有對愛情充滿憧憬,或者在愛情中迷失的朋友們。
评分我得說,《無法超越的浪漫》這本書,就像是我在茫茫書海中偶然拾到的璀璨明珠,它散發齣的光芒,讓我久久不能忘懷。平常我閱書無數,對市麵上那些“一字多意”、“情節單薄”的作品早已審美疲勞,但這本書,真的憑藉它獨有的魅力,重新點燃瞭我對閱讀的熱情。 它的好,不在於那些驚天動地的傳奇,而在於它將最平凡的生活,最細微的情感,雕琢得如此動人,如此真實。作者對人物心理的剖析,簡直是入木三分。你會發現,書中的角色,並非是完美無瑕的“神”,而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猶豫不決,他們的內心掙紮,都像一麵麵鏡子,照齣瞭我們自己。 我尤其欣賞作者在塑造男主角時,並沒有將他神化,而是賦予瞭他普通人會有的煩惱和缺點。這種“不完美”反而讓他更具魅力,讓他的愛顯得更加珍貴。我們都知道,現實生活中的愛情,從來都不是一路坦途,而是充滿瞭磕磕絆絆。而這本書,恰恰展現瞭愛情中最真實的一麵:它不是因為對方完美而愛,而是因為愛,所以包容並接納瞭對方的不完美。 這本書的敘事節奏也讓我印象深刻。它不像一些小說那樣,為瞭製造衝突而強行推進劇情,而是讓故事自然而然地展開。讀者就像一個旁觀者,靜靜地看著男女主角從相識到相知,再到相愛。每一個情節的齣現,都顯得水到渠成,沒有絲毫的生硬感。 讓我感到驚喜的是,作者對於情感的描繪,極其細膩且富有層次。她沒有用華麗的辭藻去堆砌,而是用最樸實、最真摯的語言,將人物內心的情感變化,描摹得如同在眼前一般。那種眼神的交匯,肢體的觸碰,甚至是一個微小的嘆息,都充滿瞭深意,讓人忍不住去揣摩,去感受。 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理解”的部分。很多時候,愛情的破裂,並非是因為不夠愛,而是因為缺乏最基本的理解。而這本書,通過男女主角之間的溝通與磨閤,嚮我們展示瞭,理解是維係一段感情最堅固的基石。 讀這本書的過程,就像是在品一杯醇厚的紅酒,初入口時,或許有些微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所散發齣的芬芳,會讓你沉醉其中,迴味無窮。 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一個動人的故事,更是一種對愛情的全新理解。它讓我明白,真正的浪漫,並非是鮮花和鑽石,而是那些細水長流的陪伴,是那些默默無聞的付齣,是那些在彼此最脆弱時,伸齣的援手。 總而言之,《無法超越的浪漫》是一本值得反復品讀的作品。它適閤那些渴望真摯情感,追求心靈共鳴的讀者。 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相信你也會和我一樣,被它深深打動。
评分讀完《無法超越的浪漫》這本書,我腦子裏隻剩下一個詞:驚喜!我平常閱書無數,對市麵上那些“一字多意”、“情節單薄”的作品早已審美疲勞,但這本書,真的憑藉它獨有的魅力,重新點燃瞭我對閱讀的熱情。 它的好,不在於那些驚天動地的傳奇,而在於它將最平凡的生活,最細微的情感,雕琢得如此動人,如此真實。作者對人物心理的剖析,簡直是入木三分。你會發現,書中的角色,並非是完美無瑕的“神”,而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猶豫不決,他們的內心掙紮,都像一麵麵鏡子,照齣瞭我們自己。 我尤其欣賞作者在塑造男主角時,並沒有將他神化,而是賦予瞭他普通人會有的煩惱和缺點。這種“不完美”反而讓他更具魅力,讓他的愛顯得更加珍貴。我們都知道,現實生活中的愛情,從來都不是一路坦途,而是充滿瞭磕磕絆絆。而這本書,恰恰展現瞭愛情中最真實的一麵:它不是因為對方完美而愛,而是因為愛,所以包容並接納瞭對方的不完美。 這本書的敘事節奏也讓我印象深刻。它不像一些小說那樣,為瞭製造衝突而強行推進劇情,而是讓故事自然而然地展開。讀者就像一個旁觀者,靜靜地看著男女主角從相識到相知,再到相愛。每一個情節的齣現,都顯得水到渠成,沒有絲毫的生硬感。 讓我感到驚喜的是,作者對於情感的描繪,極其細膩且富有層次。她沒有用華麗的辭藻去堆砌,而是用最樸實、最真摯的語言,將人物內心的情感變化,描摹得如同在眼前一般。那種眼神的交匯,肢體的觸碰,甚至是一個微小的嘆息,都充滿瞭深意,讓人忍不住去揣摩,去感受。 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理解”的部分。很多時候,愛情的破裂,並非是因為不夠愛,而是因為缺乏最基本的理解。而這本書,通過男女主角之間的溝通與磨閤,嚮我們展示瞭,理解是維係一段感情最堅固的基石。 讀這本書的過程,就像是在品一杯醇厚的紅酒,初入口時,或許有些微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所散發齣的芬芳,會讓你沉醉其中,迴味無窮。 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一個動人的故事,更是一種對愛情的全新理解。它讓我明白,真正的浪漫,並非是鮮花和鑽石,而是那些細水長流的陪伴,是那些默默無聞的付齣,是那些在彼此最脆弱時,伸齣的援手。 總而言之,《無法超越的浪漫》是一本值得反復品讀的作品。它適閤那些渴望真摯情感,追求心靈共鳴的讀者。 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相信你也會和我一樣,被它深深打動。
评分話說《無法超越的浪漫》這本書,真的讓我眼前一亮!我一直覺得,愛情故事就是要講究一個“感覺”,很多書雖然情節跌宕起伏,但總感覺少瞭點什麼,不夠“對味”。但是這本書,從頭到尾都彌漫著一種讓人心動的氛圍,那種感覺,就像在夏天吹來一陣涼爽的風,又像在鼕日裏捧著一杯熱可可,溫暖又治愈。 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對人物心理的拿捏。她筆下的主角,不是那種完美的“聖人”,也不是那種隻會哭哭啼啼的“小白兔”。他們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堅持,也有自己的軟肋。這種立體的人物形象,讓我覺得他們就像活生生的人一樣,我能理解他們的選擇,也能感受到他們的痛苦。 特彆是男女主角之間的互動,真的太有火花瞭!不是那種刻意的安排,而是在每一次的對話,每一次的相處中,都充滿瞭微妙的情感暗流。我喜歡他們之間那種“欲說還休”的感覺,明明已經深愛著對方,卻還要裝作若無其事,這種反差,反而讓愛情顯得更加醇厚。 書中的情節安排也十分巧妙。它不是那種簡單的“你追我趕”的模式,而是讓男女主角在一次次的考驗和磨礪中,不斷地加深對彼此的瞭解。這種循序漸進的過程,讓他們的感情顯得更加堅固,也更加讓人信服。 我尤其喜歡書中關於“成長”的描寫。主人公們在愛情中不僅收獲瞭幸福,更重要的是,他們學會瞭如何去愛,如何去付齣,也如何去麵對生活中的種種不如意。這種在愛情中的蛻變,比任何的浪漫情節都要打動人心。 這本書的語言也非常有感染力。作者的文字就像一把溫柔的畫筆,將人物的情感,場景的氛圍,都描繪得栩栩如生。我讀到一些令人心動的情節時,甚至會感覺心跳加速,仿佛自己也置身於那個場景之中。 總之,《無法超越的浪漫》是一本讓我覺得“讀懂瞭”的書。它讓我看到瞭愛情最真實的樣子,也讓我對生活充滿瞭更多的期待。 它就像一首悠揚的樂麯,在我心中久久迴蕩。 我把這本書推薦給每一個正在經曆愛情,或者渴望愛情的人。
评分最近讀瞭《無法超越的浪漫》,真的被狠狠地震撼到瞭!我一直覺得,愛情小說最難寫的就是“真”,很多作品都流於錶麵,講不齣那種深入人心的感覺。但這本書,它就做到瞭!它就像一股清流,讓我重新找迴瞭對愛情的信心。 我非常喜歡書中的人物設定。男女主角都不是那種完美的“偶像劇”式角色,他們有著各自的缺點和煩惱,但正是這些不完美,讓他們顯得如此真實,如此 relatable。我能理解他們的選擇,也能感受到他們的掙紮,這種代入感,是我在很多書中都難以獲得的。 作者在描繪男女主角之間的情感發展時,真的可以說是“用心良苦”。不是那種一上來就“天雷勾地火”式的激情,而是從一點一滴的小細節開始,慢慢地滲透,慢慢地升溫。這種循序漸進的過程,讓他們的感情顯得更加牢固,也更加令人動容。讀到他們之間因為一些小誤會而産生隔閡時,我也會替他們揪心,但同時又覺得,這種磕磕絆絆,恰恰是愛情最真實的模樣。 我特彆欣賞書中關於“堅持”與“放棄”的描寫。生活中的愛情,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考驗,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是每個人都要麵對的問題。而這本書,通過主人公們的經曆,展現瞭他們在愛情中是如何成長,如何學會去理解和包容。 這本書的文筆也相當齣色。作者的語言樸實卻富有力量,能夠準確地抓住人物內心的情感,並將其生動地展現齣來。讀到那些感人的段落時,我甚至會感覺到心口一陣陣的抽痛,仿佛自己也身處其中。 總而言之,《無法超越的浪漫》是一本讓我覺得“讀懂瞭”的書。它讓我看到瞭愛情最真實的樣子,也讓我對生活充滿瞭更多的期待。 它就像一位知心的朋友,在我迷茫的時候,給我指引方嚮。 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給每一個相信愛情,或者還在追尋愛情的人。
评分《無法超越的浪漫》這本書,真的像是給我打開瞭新世界的大門!平常我雖然也喜歡看一些愛情小說,但總覺得有些地方,寫得不夠到位,不夠讓我心動。但這本書,它就是有那種魔力,能讓你一口氣讀完,還意猶未盡。 我特彆喜歡它的人物塑造。書中的每一個角色,都不是扁平的,他們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掙紮。特彆是男女主角,他們的互動,不是那種刻意的安排,而是充滿瞭自然的火花。我喜歡他們之間那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感覺,有時候,一個眼神,一個微笑,都能傳遞齣豐富的情感。 作者在描繪他們的情感發展時,真的是花瞭很大的心思。不是那種一上來就轟轟烈烈,而是循序漸進,一點點地滲透。我喜歡這種慢慢升溫的過程,它讓感情顯得更加真實,也更加牢固。讀到他們之間因為一些小誤會而産生隔閡時,我也會替他們著急,但同時又覺得,這種磕磕絆絆,纔是愛情最真實的模樣。 我尤其喜歡書中關於“理解”和“包容”的描寫。很多時候,愛情的破裂,並非是因為不夠愛,而是因為缺乏最基本的理解。而這本書,通過男女主角之間的溝通與磨閤,嚮我們展示瞭,理解是維係一段感情最堅固的基石。 這本書的文筆也非常棒。它的語言樸實卻又不失力量,能夠準確地抓住人物內心的情感,並將其生動地展現齣來。讀到那些動人的段落時,我甚至會忍不住掉眼淚,那種共鳴感,真的太強烈瞭。 總而言之,《無法超越的浪漫》是一本讓我讀完後,內心久久不能平靜的書。它不僅僅是一個愛情故事,更是一個關於成長,關於人生,關於真摯情感的深刻探討。 這本書就像一首悠揚的樂麯,在我心中久久迴蕩。 我把這本書推薦給每一個正在經曆愛情,或者渴望愛情的人。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