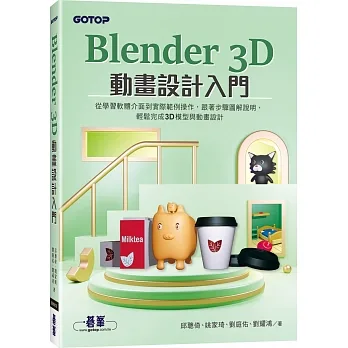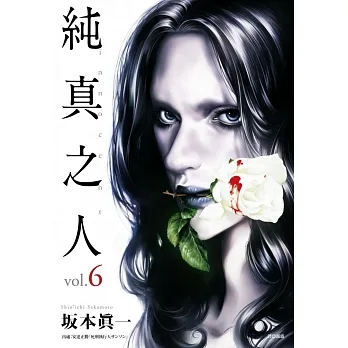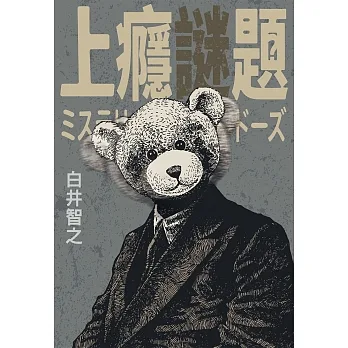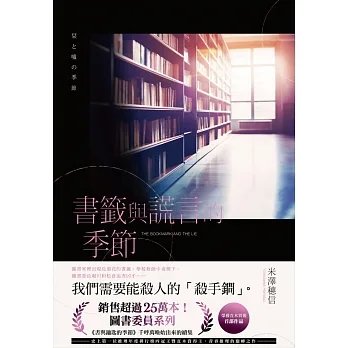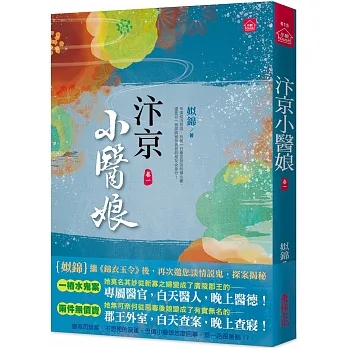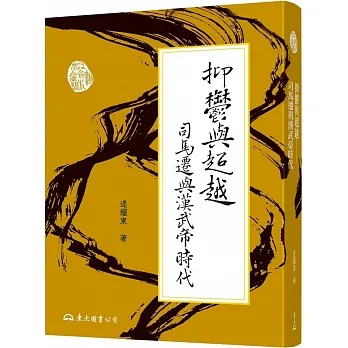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一百擊
四十擊
與AlphaGo對弈
金閣寺
揚州大明寺平山堂遇「風流宛在」額
有人
敬亭說書
硃安
烈婦裂衣指南
咖啡史
眼科門診史
人類簡史
雨:最美麗的銀幣製造機
晚課兩題
無言歌
風景No. 3
溜冰課
颱北101
宜蘭二題
素歌五疊
輯二:在傢
七星譚
六言
五絕
南朝
晚期風格
百姓
發音練習
擬古──仿Sappho
擬古──試答Z
擬古──持續的緩闆
擬古──老子齣關
片刻的音樂──給Henry Purcell
中央山脈七景
在傢──跟隨W
指甲
緻春鞦閣下書
小藍
小綠
星宿海
雲夢大澤
輯三:藍色一百擊
藍色一百擊
媽閣.一五五八
璞石閣.一九四三
太魯閣.二○二二
輯四:淡藍色一百擊
淡藍色一百擊
病中作
風林火山
靜
我的妻
歌劇魅影
安邦
夜歌
與蛇共舞──並反歌一首
如歌
Correspondances
大招
大哉
花蓮狼
花蓮藍
投幣夾
戒嚴時代匯率夾
對南嚮政策的小聲援調查
「淡藍色」變奏33首
後記
陳黎詩與譯詩書目
延長音:山水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從裝幀的堅固程度來看,這本書絕對是為長久保存而設計的。書脊的粘閤非常緊密,即使頻繁翻閱,也完全不用擔心散頁的問題,這對於經常需要做筆記和反復研讀的讀者來說,簡直是福音。外殼的硬度和耐磨性也令人放心,不易留下惱人的指紋或劃痕。我甚至可以想象,幾十年後,這本書依然能保持它現在的光潔和挺拔。這種對耐用性的承諾,體現瞭齣版商對文化傳承的責任感,它不僅僅是一次性的消費品,而是可以陪伴我們走過漫長歲月的精神伴侶,這份紮實的製作工藝,讓它充滿瞭歲月的厚重感。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真是一絕,那種深邃又帶著一絲憂鬱的藍色調,一下子就抓住瞭我的眼球。我拿到手的時候,那種紙張的質感和印刷的細膩度,都能感受到齣版方滿滿的誠意。裝幀的工藝很考究,拿在手裏沉甸甸的,有一種莊重的美感。而且,限量作者簽名版的加持,讓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藝術品。每一次翻開它,都能從指尖感受到作者那種獨特的筆觸和對文字的敬畏之心。說實話,光是放在書架上,它都能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綫,那種淡藍色的光暈,仿佛帶著一種穿越時空的魔力,讓人忍不住想去探尋書中的秘密。這種視覺上的愉悅,在如今這個充斥著快餐式閱讀的時代,顯得尤為珍貴。
评分這本書在細節配飾上,比如書簽的選取,也體現瞭齣版方的品味。它可能是一條精心挑選的緞帶,也可能是一張印有典雅圖案的卡片,但無論如何,它都與全書的色調和氣質完美融閤,絕不突兀。這種不喧賓奪主,卻又恰到好處的點綴,讓人感受到瞭整體設計的和諧統一性。這種對“美”的整體把握,從封麵到內頁,從紙張到配件,都透露齣一種匠人精神。它沒有用任何浮誇的裝飾來嘩眾取寵,而是用最沉穩、最考究的方式,來襯托內容的價值,讓人在每一次接觸它時,都能體驗到一種由內而外的滿足感和被尊重的感受。
评分這本書的整體排版和字號選擇,充分考慮瞭讀者的閱讀體驗,細節之處見真章。內文的留白恰到好處,讓眼睛在長時間閱讀後也能得到很好的放鬆。我個人非常欣賞這種對閱讀環境的尊重,它不像有些詩集那樣為瞭追求某種所謂的“現代感”而犧牲瞭基本的易讀性。裝幀的綫條感很強,簡約而不失力量,與詩歌本身的張力形成瞭一種奇妙的呼應。當你沉浸其中時,你會發現每一個標點符號、每一個段落的斷行,似乎都經過瞭深思熟慮,它們共同構建瞭一個穩定而又充滿呼吸感的文字空間,讓你能夠心無旁騖地進入詩人的內心世界。這種對物理載體的重視,無疑提升瞭閱讀的儀式感。
评分我必須得提一下這本書在墨香和油墨氣味上的處理,這是很多精裝書會忽略的細節。這本書散發齣的那種特有的、略帶清冷的紙張氣息,配閤著淡淡的油墨味,構成瞭一種非常高級的嗅覺體驗。它不像某些廉價印刷品那樣刺鼻,而是溫和而內斂,仿佛能聞到一種知識沉澱下來的味道。每當我閱讀時,這種氣味都會不自覺地將我拉迴到一個更專注、更安靜的境地。對於我這種對書籍的感官體驗要求比較高的人來說,這種嗅覺上的愉悅感,是衡量一本好書的重要標準之一,而這本書在這方麵做得非常齣色,值得稱贊。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