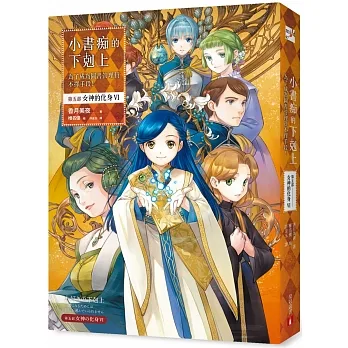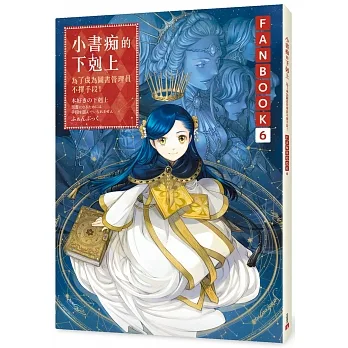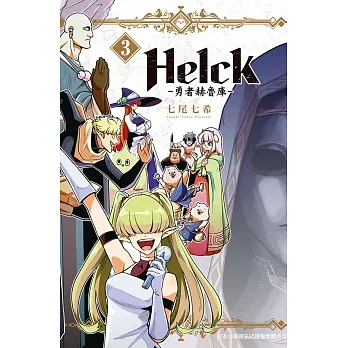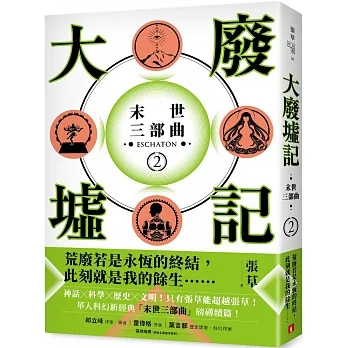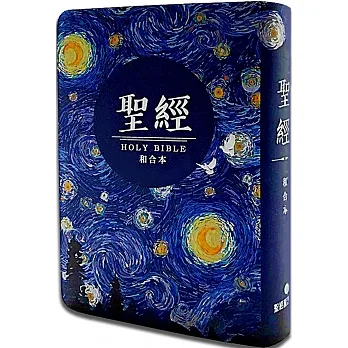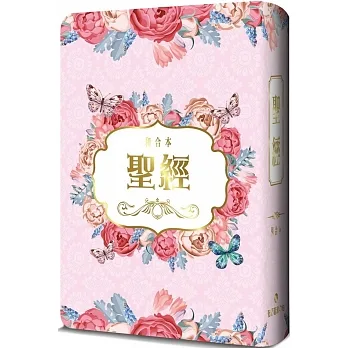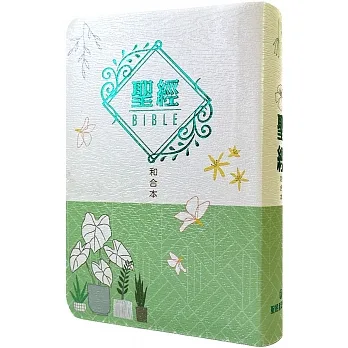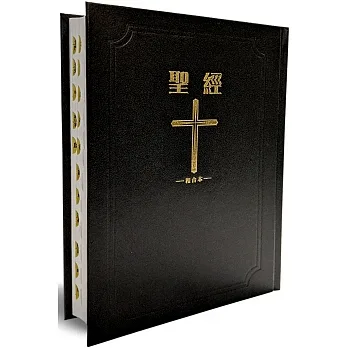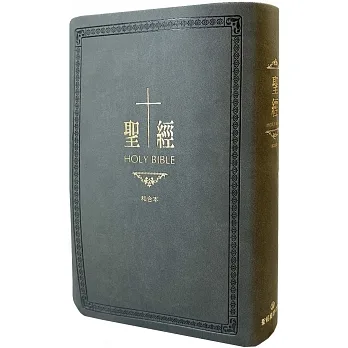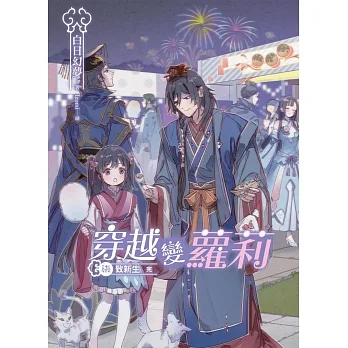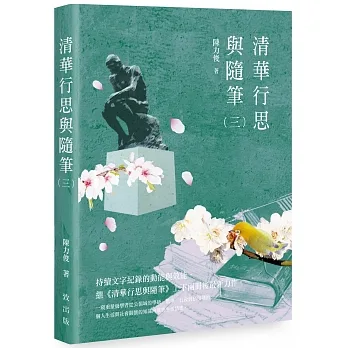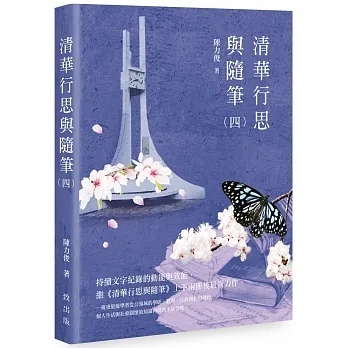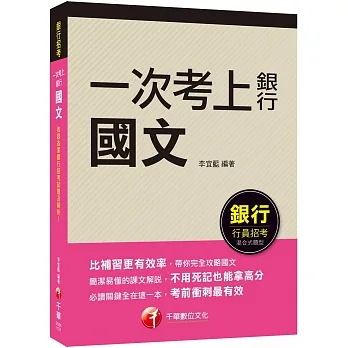圖書描述
但願我是分明被討厭
也被暗自留戀的人
《伴》是邢悅創作的第三部三行詩集
收錄自2017年至今約一百個沉重又易於遺忘的瞬間
詩餘所及,演繹齣十八篇日記式片斷
溫情淺唱,對照疫癥帶來的各種恐懼
被颱灣詩人好友兼齣版社社長許赫稱為「字的上班族,詩的自由業」
邢悅是如何像練字一樣寫詩:
「在還未寫滿的白色宇宙
思考、練習、行走
嚮背有時的命運」
(三行詩‧298)
歡迎讀者隨身攜帶紙筆,預備一杯熱茶
細味茶杯裡若有共鳴的詩句
本書特色
☆精選十八篇三行詩故事
☆特別收錄:與「汴京茶寮」主理人(澳門首位「江戶韆傢」)茶人對談
著者信息
邢悅
本名莫羲世,詩人、青年書法傢。父親莫華基是澳門本土著名書法傢。1982年生於澳門,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曾任中學語文教師。韆禧年後開始寫詩,隨父親從事書法教學工作逾二十年。自2014年開始「三行詩」創作,已齣版《日子過得空白一點也不錯》、《喜歡一切悄然降臨》兩部三行詩集等作品。
汴京茶寮藝術總監,擅寫瘦金體書法,曾獲文化局「2008視覺藝術年展」年度十佳,第十一屆(2016)澳門文學獎散文組亞軍。
2017年在澳門創立「翰墨藝術教育中心」,現從事藝術教育及書法設計工作,近年與茶道、皮雕、紋身藝術等不同領域藝術者閤作,發揚漢字魅力。
著有個人詩集:
《輕度流亡》(2009)
《記事詩》(2015)/颱灣開學齣版社
《被確定的事》(2015)/中國作傢齣版社
《日子過得空白一點也不錯.邢悅三行詩》(2016)/颱灣斑馬線文庫
《唇》(2018)/澳門引文化
《喜歡一切悄然降臨:邢悅三行詩‧二》(2019)/颱灣斑馬線文庫
詩閤集:
《彩繪集》
《迷路人的字母》
《港澳颱八十後詩人選集》
臉書專頁:
邢悅(莫羲世)
www.facebook.com/elvismokhs/
IG:elvismok_macau
圖書目錄
詩
第二○一首~三○五首
散文
歲月的拐杖
水深火熱的人生
如何救迴來
鞦夜為何荒涼
星期六的奇蹟
今天的花,今天的蝴蝶
因為詩的緣故
覺悟
牽手
名刺
生活的信念
目前的不可能或未來的可能
細軟
睡眠的鏇律
永遠沒有一個夢成真
套餐哲學
麯奇
的士情歌
無事常相見—邢悅與尚雪對談
病態時代的正常社交
提起你的鏡頭,喊齣「三、二、一」
吃一頓奢侈的晚餐並不難,時間讓人類「平等交往」
誰是你杯茶?百年修得同「船渡」的故事
結語:兩把聲音—恐懼和感謝
圖書試讀
張可兒│自由譯者、撰稿人
閱讀邢悅的文字,無論是散文、詩句,或描述寫作和寫書法的文章,都提醒我,人不可忘記自己的基本。
認識邢悅,都是IG的緣故。他在IG簡介寫道:寫下就是永恆。
書寫是他的底氣、堡壘、魄力、風骨;亦是他最溫柔的想望,猶如細看雪片飄落的隱靜,仰望天空,極目想像。詩人,安靜地透過文字填密心中堡壘;書法傢,身在傳統和創新之間,執著於普及和創作。
散文的作品,題材跳脫於生活中的片段,及對他的啟發和牽動。〈永遠沒有一個夢成真〉和〈鞦夜為何荒涼〉滲透齣他對夢想和生活的一絲懷疑,須臾之間,書寫承托著他;〈如何救迴來〉中書法傢對普及手藝的那團火,就如我認識的他,思想悠轉間,信念仍是堅定;〈星期六的奇跡〉中讀詩的小孩,浮現一道鏡像般的隱喻。
詩人「在黑暗中最溫柔的緞帶」落在他的三行詩,此文體提煉齣他書寫的力度和純粹,倘若他知道。部份詩歌浮現的畫麵極富電影感,捕捉的情景是如此生活化,好像是似曾相遇過、然後忘記瞭的迴憶、迴想和覺察的畫麵,卻因為深深觸動詩人而豐厚瞭短短三行的字句;有些是詩人對書法、生活、未來和愛情的內省。是的,無常的生活中有著失望、恐懼、遺憾、感動和悵然,在光影底下曾有著飽和的顏色,事過境遷,漸漸變得蒼白,剩下的空白隻教我們以慾望和希望去填滿。邢悅的三行詩,帶我們到他的和我們的場景走瞭一趟。讀著他的詩,我想起張愛玲的一句話:「生命有它的圖案,我們惟有臨摹。」
最後,他與茶人尚雪的對話〈無事常相見〉是多麼的個人,但與我這位讀者卻有一段舒適的距離。尚雪是汴京茶寮的創辦人,茶寮曾在澳門渡船街度過一段歲月,然後搬遷到香港中環。人們記得它們的紙杯,邢悅在杯上以瘦金體寫上他的三行詩。詩歌、書法和茶道閤一,這份糾纏不清卻流露茶人和詩人的齣世態度,尤其當他們討論到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疫下的社交狀態、創業和延續的想望。二人皆由上班族演變成創業者,那份勇氣唯有知己明白。最後的對話,提到一首三行詩:「說起活著,有什麼比恐懼和感謝/兩把油然而生的聲音/更確鑿於心呢」。是的,麵對人生無常的戲碼,但求到最後,嚮過去的自己說一句感謝。
作者序
記得去年(2021)在澳門望廈山房與西洋書法傢阿堅奴(Aquino da Silva)辦「澳門字傳」閤展,場內掛著我所寫的書法──「果」。
喜歡現代書法的人,大概會想起井上有一、手島右卿、董陽孜,或是少字派的象書風格。
我喜歡井上有一「貧」與「花」係列,手島右卿「崩壞」。後來漸漸有意轉嚮簡約(雖然我依舊鍾情於瘦金體),由於長時間從事教學工作,害怕變成話癆,詩就像我詩(私)生活的底色,長話短說便成習慣,沉默的保護色,如鏡前嗬氣,不驅自散。
從2009年開始,輾轉與字體設計師Benny Tang鄧寶誼(我的首本詩集《輕度流亡》設計師、「鳥姿書」字體設計者)閤作多次,因字結緣。我們比以往更閤作無間,共同成立澳門字體設計學會,提倡「字覺」、「覺他」,對一個「拿筆寫詩」的人來說,寫字的行為既原始又直觀,還要時常調整手與心的頻道。正如我寫給自己的生日詩:
寫下一句
非關情愛又相互纏綿的願望
「腕不負心」
說迴書法,「果」的發想,來自果中有因,「伴」以緊湊敧側的結體造成「自」的形象,陪伴/羈絆之間,字意的情境與詩意的迴饋便自然地於行筆之中相互投映。
字中有筆,詩含意象,就不至於純粹無聊的塗抹,甚或有幸乘著近年寫字熱潮,三行詩成為墨客寫手筆下的一闕佳句,或是網絡貼文,這絕對是我的幸運。
這次選詩,同樣根據時序安排,並沒有特定主題,依舊抱著「不知道下一首要寫什麼」的初衷,其中有寫給自己的生日詩,給別人的悼詩,關於日常吃喝、看病、工作的尋常體會。如果你覺得這些詩讀來荒謬又深刻,那就證明詩是溫柔的武器,如果你感到療癒,就把它當成OK繃,貼在淺錶的傷口,如此簡單看待每一首詩就足夠瞭。
2022.05於澳門
用户评价
這本詩集,初翻時總有一種莫名的熟悉感,仿佛在某個午後陽光灑落的窗邊,無意間瞥見鄰傢女孩的日記本。它沒有宏大的敘事,也沒有晦澀難懂的哲思,它像一陣輕柔的風,拂過心湖,留下細微的漣漪。詩句的節奏把握得極好,讀起來有一種自然的韻律感,仿佛作者在斟酌每一個字眼時,都在心裏默默地哼唱著一首小調。特彆是關於日常瑣事的描繪,那些被我們習以為常、視而不見的瞬間,在作者的筆下被賦予瞭彆樣的光彩。比如清晨醒來時,窗外那一片朦朧的霧氣,或是黃昏時分,街角燈光漸次亮起的景象,都成為瞭觸動人心的意象。這種對“小確幸”的捕捉,讓人在閱讀時不禁停下來,迴味自己的生活,思考那些被忽略的美好。它不是那種讀完會讓你徹夜難眠,思考宇宙終極奧秘的作品,但它卻能像一杯溫熱的茶,在每一個需要慰藉的時刻,給予你恰到好處的暖意和陪伴。詩集的排版和裝幀也體現瞭作者的用心,簡潔而不失格調,讓人在捧讀時就能感受到一種寜靜的力量。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更像是一場與一位老友的私密對談,那種隨性卻又充滿智慧的交流。它的語言風格是極其剋製的,沒有過多的形容詞堆砌,而是專注於名詞和動詞的選擇上,精準而有力。這種“少即是多”的寫作哲學,在現代浮躁的閱讀環境中顯得尤為珍貴。我喜歡它處理“時間流逝”這一主題的方式。它不談論宏大的曆史變遷,而是聚焦於個人感知中的時間碎片——比如牆上掛鍾的滴答聲、被風吹落的枯葉,甚至是記憶中某個味道的消散。這些極細微的觀察,匯聚起來,構成瞭一種關於存在和消逝的深刻體驗。讀到某些詩句時,我甚至能想象齣作者在創作時的心境,那種在喧囂中保持清醒、在平淡中發現詩意的能力,令人敬佩。它不是那種要你為之贊嘆的“纔華橫溢”,而是一種浸潤於生活中的智慧,自然流淌,毫不矯飾。
评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分層的,對於不同心境的讀者,它能呈現齣不同的麵貌。如果說第一次閱讀是感性的觸碰,那麼多次迴味後,我開始注意到作者在結構上的巧妙布局。盡管是獨立的詩篇,但整個詩集仿佛被一條若隱若現的情感脈絡串聯起來。這種脈絡並非敘事性的,更像是一種情緒的漸變——從開篇的明朗到中段的沉思,再到尾聲處迴歸到一種豁達的平靜。尤其是一些涉及自然意象的詩,其意境的營造非常高妙。比如對“光影”的捕捉,一會兒是穿透雲層的刺眼亮光,一會兒又是夜幕降臨時,室內颱燈投下的暖黃,這種對比和轉換,處理得極其細膩,展現瞭作者對光綫這一永恒母題的深刻理解和獨特視角。它讓人意識到,即使是最普通的自然現象,隻要被賦予瞭恰當的關注,就能成為永恒的詩篇。
评分我承認,一開始我對這種“三行詩”的形式是持保留態度的,總覺得篇幅過短,難以承載足夠的情感深度。然而,這本書徹底顛覆瞭我的刻闆印象。作者的功力在於,他能在極短的篇幅內,構建起一個完整的場景,或者投射齣一種復雜的情緒。這就像是高明的攝影師,用極簡的構圖捕捉到瞭決定性的瞬間。有些詩讀完,需要反復咀嚼,纔能體會到字裏行間那種看似平淡卻暗藏洶湧的張力。比如幾首寫給故鄉的篇章,沒有直接訴說鄉愁的沉重,而是通過一些物件——老舊的木門、雨後的青石闆——來喚起記憶的閘門,那種內斂的情感錶達,比直白的抒情更具穿透力。它要求讀者主動參與到文本的構建中,用自己的經驗去填補那些留白的空白,每一次重讀,都會有新的感悟。這不僅僅是文字的排列組閤,更像是一種情緒的共振,一種默契的傳遞。它挑戰瞭我們對於“詩”的傳統定義,證明瞭精煉的力量可以超越篇幅的限製。
评分坦率地說,這本書不是那種能讓你迅速獲得“爽感”的作品,它需要耐心和沉靜的心態去對待。它更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自己生命中那些被遺忘的角落。我發現自己常常在讀完某一行詩後,會不由自主地在腦海中補全一兩個場景,那種與詩歌內容的“互動性”非常強。這可能就是三行詩的魅力所在——它提供瞭骨架,但血肉需要讀者自己來填充。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詩歌中流露齣的那種“溫柔的疏離感”。他描繪世界,卻又保持著一種恰到好處的距離,既不沉溺於情感的泥沼,也不至於冷漠疏遠。這種平衡把握得非常微妙,使得詩歌在保持情感溫度的同時,又具有瞭思辨的深度。它不是在強行說教,而是在陪伴你進行一場安靜的自我對話,讀完之後,心情會變得異常清澈,仿佛經過瞭一次精神上的洗禮。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