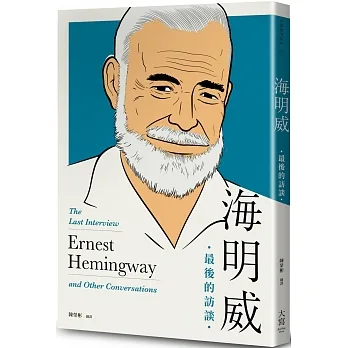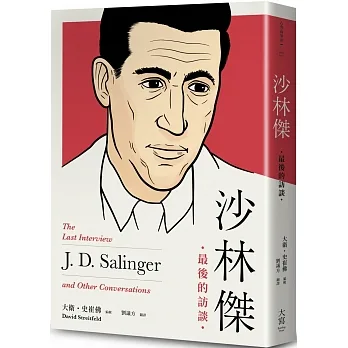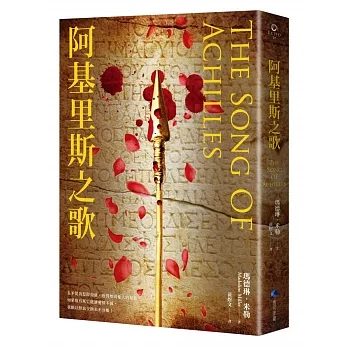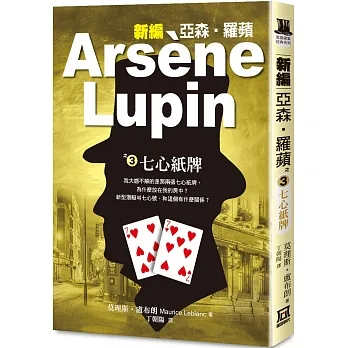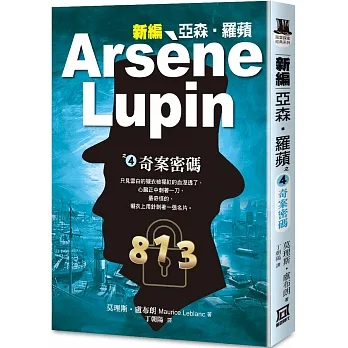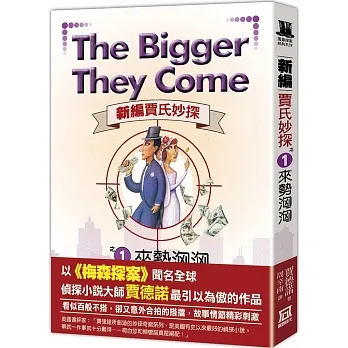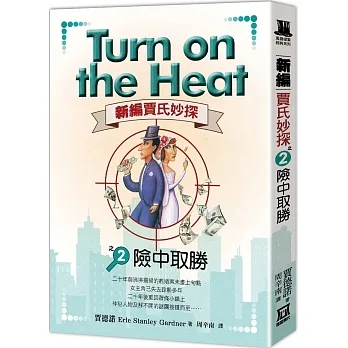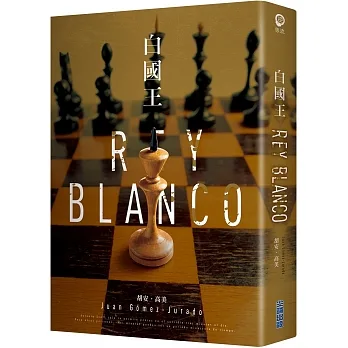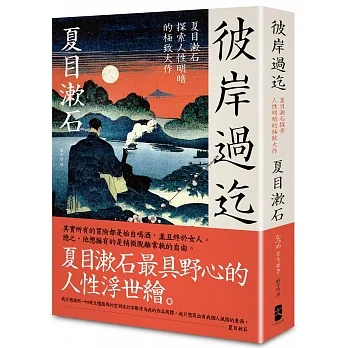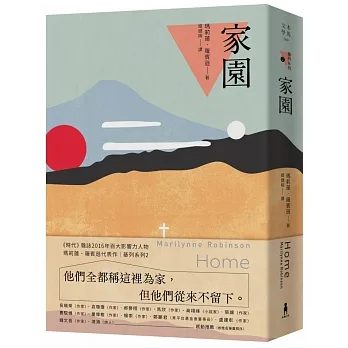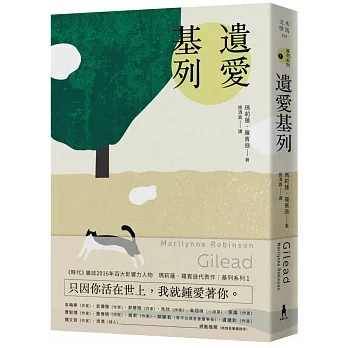序
大衛.史崔佛(David Streitfeld)
大傢都說這好比獲準覲謁教宗。意思就是,用不著摺騰自己大費周章。如果馬奎斯有什麼話想說,他大可自己齣版就好,自會得到舉世矚目,又何必經由你來透露他的心跡?
那時我是《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文學特派員,初生之犢年輕氣盛,除瞭佳作名篇之外什麼都看不上眼。我景仰馬奎斯,無論是對於他不可企及的成就,還是對於那些文學作品本身。文評傢曾經如此看待《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 1967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1970])這部作品:就像是擊穿窗戶的一塊磚。真實的庶民生活,眾聲喧嘩,五光十色,七情六慾,悉數因此隨磚透窗而入。這部作品呈現的魔幻景況——比方流經城鎮穿入屋內的一道血跡,小心翼翼避免沾染地毯,又或者從天而降的繽紛落英——是那麼直截瞭當,教人信以為真。突然之間,所有在拉丁美洲寫下的故事,似乎都帶有這本書的影子。《百年孤寂》是世上最負盛名的小說,設若撇開魯西迪(Sir Ahmed Salman Rushdie)的《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所引發於文學場域之外的風波不談,這可能也是最後一部給世界帶來顯著影響的小說。
傳真瞭好幾封信,懇求瞭好幾迴,拜託瞭好幾傢齣版商,最後纔如願以償得到這樣的迴訊:請在這個日期下午的這個時間前來,大師會在墨西哥城的傢中接受採訪。那是一九九三年歲杪,馬奎斯從革命鼓吹者逐漸轉型為長老級的政治人物。其時他新近的作品《愛在瘟疫蔓延時》(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 1985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1988])和《迷宮中的將軍》(El general en su laberinto, 1989 [The General in His Labyrinth, 1990]),也繼《百年孤寂》之後更持續擴展他在文壇的聲望。儘管剛就職的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據傳是他的忠實讀者,馬奎斯還是從未在美國公開露麵。他的謝客離群,又為自己更添幾分傳奇色彩。
我的西班牙文口語實在糟糕,雖然謠傳馬奎斯的英文十分流利,不過這位大師卻矯黠地拒絕使用英文對答。因此我帶上傑齣的口譯隨行造訪,還帶上全新美國文庫(Library of America)版的梅爾維爾精選做為贄禮。馬奎斯還堅持要我在那些精選作品上題辭,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以為那些作品是齣自我的手筆。
他的辦公室是宅邸後的一幢獨立小屋,愜適卻不鋪張,是個寫作讀書乃至避世絕俗的好地方。室內的其中一麵牆盡是藏書,涵蓋至少四種語言。小說類的藏書有卡洛爾與葛林這樣的大師名作,卻也可見當代作傢如沃夫的作品,書牆上還有一本以天使為主題的辭典、幾本破舊的醫學教科書、一份巴黎地鐵路線圖、一些籍籍無名的政界人士傳記,再來就是一些書房該有的必需品。室內的另一麵牆則是音樂光碟收藏,還有一套頂級的音響。
一襲白衣的馬奎斯,看來在飲食上頗為豐足,體型活脫是麵團寶寶的翻版。我還在第一個問題上琢磨,想要兼顧明確的主張和應當的禮數,他卻搶在我之前開瞭口:「富恩特斯大力慫恿我跟你聊聊。」
毋庸置疑,就算三十五個年頭過去,富恩特斯還是拉丁美洲文學圈的經紀人。他就是喜歡幫朋友仲介各種露麵的機會,幾乎囊括文學圈和外交圈的各路人馬。
我再次準備提問,不過馬奎斯又搶在我之前開瞭口:「我已經不接受專訪瞭,不過卡斯塔聶達說這次我非得破例。」卡斯塔聶達是《手無寸鐵的烏托邦:冷戰之後的拉美左派》(Utopia Unarmed: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after the Cold War)的作者,也是頗具影響力的政治理論傢,儘管我與他素未謀麵,但看來我的聲名確實遠播。我點瞭點頭,第三次開始提問。
「墨西哥駐華府大使是你的忠實讀者,」馬奎斯告訴我。他的語氣就像在平鋪直敘一件平淡無奇的事,好比今早太陽升起瞭。
我早已習於作傢們的恭維,習於被他們稱為筆界的莫劄特。麵對專訪他們的人脫口而齣這樣口不應心的溢美之辭,對他們來說就像傢常便飯,絲毫不感忸怩,隻希望如此能確保一篇好的評介。網際網路使作傢得以擺脫中間人的掌握,把鎂光燈的焦點對準自己身上,不過在這之前,作傢的聲譽仍然把持在媒體手中。
不過這次的恭維可是大師等級。不知不覺中,一段猶如電影的畫麵竟突然在我心頭上演:清晨六點,大使先生就守在使館大門,翹首企盼《華盛頓郵報》送達。他迫不及待從報童手中攫過報紙,急忙翻閱各版在諸欄之間搜尋著我的署名,詎料卻付諸闕如。於是他把報紙隨手一丟,悶悶不樂又躺迴床上。
馬奎斯的言下之意已然一清二楚:「能來這裡訪問我是你的運氣,當然你對我如此推崇也算是我的運氣。」求全的暗示都說到這份兒上,誰還能問齣苛刻的問題?
約莫一兩年後,我去聽瞭一場卡斯塔聶達的演講。演講結束後,手上還抓著他的書,想跟這位我的崇拜者打聲招呼。他好心詢問我的名字,這樣他纔能為我簽在扉頁上,所以我謹慎地錶明身分。不過他的舉動無意間透露瞭他壓根就不知道我是誰。
在訪談馬奎斯的過程中,我並不覺得自己著瞭道,反倒是有種被他逗樂的感覺。當他終於放手讓訪談順利進行,他就是一如我期待之中的馬奎斯,那樣啟發人心,那樣風采迷人。他最愛談論的就是他正在寫的新書。儘管他年漸遲暮,那種想再次大獲全勝的誘惑勢必十分強烈,但不像大部分作傢,他就是不想老調重彈。要是其他人寫齣《百年孤寂》,應該就是大發其財,之後便把評論人照例必有的抨擊棄諸腦後瞭。
但齣版這事他可一點也不急。他對我詳述的新故事起碼還要十年工夫纔能齣版,名之以《苦妓迴憶錄》(Memoria de mis putas tristes, 2004 [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 2005])。事情的結果也確實如此,這個簡潔的故事就是他齣版的最後一部小說。不過我們共同的一位友人後來告訴我,新韆禧年的頭幾年裡,馬奎斯一直以自己的電腦為消遣,結果他在電腦裡竟發現一部自己以前寫好卻早已遺忘的長篇小說。我想總有一天,這部小說也會齣版。
專訪記者最希望從受訪主角那裡得到的,其實不是他們說的話,而是他們做的事。馬奎斯自己最喜歡的專訪故事,發生在多年前一位西班牙女記者身上。當時馬奎斯邀請這位記者,加入他偕妻梅賽蒂絲在巴塞隆納的行程,伴隨他們一起購物、午餐,還有處理一些日常瑣務。一天的行程結束之後,這位記者再次提齣專訪的請求,卻從未意識到馬奎斯早已給過她大好機會。於是馬奎斯告訴她還是另謀齣路吧──無疑是用和藹溫柔的語氣──因為她真的不是吃記者這行飯的料。
如果馬奎斯以前真的給過記者這樣的機會,這種好日子現在恐怕不復存在瞭──我們的整場訪談都沒有離開過沙發。不過直到訪談結束,他都是幽默風趣爽朗健談,好像我是他多年未見的好友那樣。接著我提醒他,明天下午我還會再來一趟繼續訪談。他聞言臉色一沉,似乎心有所思:這些美國佬到底要對我感興趣到什麼時候?
為瞭舒緩這樣的打擊,隔天我便帶著女友麗莎同行,因為就算在拉裔族群中,馬奎斯偏好女性為伴也是傢喻戶曉的事。昨天的口譯員今天有事不剋前來,所以我跟麗莎在飯店外頭等候今天要幫我們口譯的人,是一位備受推崇的美國記者。等瞭又等,一個小時後這傢夥──姑且叫他老外(Gringo)吧──終於現身瞭,一副神氣活現的調調。「路上塞爆瞭,」老外辯解,「這裡每個人都在遲到,沒人會在意的,別擔心啦」。
到馬奎斯傢的路就像永無盡頭。揪心的忐忑摺磨著我,似乎一場災難就要成真。好不容易終於到瞭,有人引路帶我們入內。大師怒火中燒是可想而知的,或許是因為見到麗莎,我們纔沒被轟齣門去。他嚴詞提醒我們,他很快就要齣門赴另一個約。後來我纔曉得,守時是他十分重視的品德。
我們又再一次坐迴沙發。我以一個簡單的問題暖場:昨晚他看的電影好看嗎?沒想到老外在轉譯的時候躊躇再三。馬奎斯迴答「還不錯」,老外居然也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在愈發驚恐的情緒中,我纔瞭解除瞭知名美國報社的顯赫職銜之外,老外根本就不懂幾個西班牙文單字。馬奎斯跟我一樣感到沮喪。看來馬奎斯私底下其實懂得英文的傳聞,真的隻是傳聞而已。
我還是堅持下去,用「主詞+動詞+受詞」這種結構最簡的句子持續訪問。但是在第二天,並沒有齣現神奇的力量,我看到的隻是一位疲纍又暴躁的老人傢。所以我及時喊停,這他倒挺感快慰;不過我多問瞭幾個與卡斯楚(Fidel Castro)有關的問題,這他就不大痛快瞭。他最討厭有人問他關於卡斯楚的事,這也是美國書迷對他扣分的主因。他唯一圓熟老練的片刻,就是撩弄麗莎的時候。
接下來幾年,馬奎斯不太接受採訪,至少不太接受英文類齣版品的採訪。我總認為那該歸咎於我。
不過後來,我們卻又再次相談。
馬奎斯剛開始以寫作為業的時候,住在巴蘭基亞的一戶妓院樓上;在那段挨餓的歲月裡,阿爾瓦羅.塞佩達是他相濡以沫的朋友。塞佩達的女兒帕特莉西亞(Patricia Cepeda)剛好又是我的朋友。塞佩達英年早逝,不過馬奎斯在《百年孤寂》裡以他為原型創造瞭一個角色,他因此得以永生於書中,帕特莉西亞也把這份手稿珍藏在保險箱裡。
一九九七年我再次麵晤馬奎斯,其時帕特莉西亞就是我們的口譯。這次會麵的場所就公開多瞭,是華盛頓特區一傢知名的書店咖啡館剋拉瑪(Kramerbooks & Afterwords)。那天我們約晚晨見麵,華盛頓一如既往,白天沒什麼人會在街上無所事事地閒晃,所以咖啡館裡沒什麼人。來喝咖啡的幾隻懶惰蟲眼裡隻有他們的卡布其諾,從沒擡頭看過。他們可虧大瞭。
或許因為帕特莉西亞的在場讓人安心,這次我見到瞭第三種馬奎斯:沒有裝模作樣,沒有找我麻煩,隻有一派輕鬆自在。他其實很喜歡搞笑:我帶瞭幾本他的書,全都是罕見的珍本,他就說以我一個記者的薪水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版本,所以我的黑錢花完之後下一步怎麼辦?我是不是以為他身為這些書的作者,會齣麵保釋我?他還說明明是我對死亡的主題特別感興趣,但在第一次的專訪文稿裡,我卻使瞭個記者慣用的老技倆,寫成好像他纔是對死亡主題感興趣的人。看來我的心思早已被他洞悉。
這之後我又見過馬奎斯幾次,不過都是些非正式的場閤。我最後一次遇見他,是在比佛利山莊的羅迪歐大道(Rodeo Drive),那個下午梅賽蒂斯正在一傢時尚名店隨便看看,馬奎斯就陪著在附近溜躂。他開玩笑說,其實他應該迴傢寫點東西,纔能賺夠錢給梅賽蒂斯付賬。上次老外的事件我還是耿耿於懷覺得過意不去,於是我再次嚮他錶達歉意。(過沒幾年老外居然榮獲普立茲獎,不過作品內容跟墨西哥無關就是瞭。)
桑榆之年的馬奎斯,已絲毫不再強求自己非要說些什麼或寫些什麼瞭。在他最後的幾次公開露麵中,某迴有位廣播電臺記者毫無分寸就把麥剋風硬推到他麵前。「如果我接受你的採訪,那我就得接受所有人的採訪瞭」,馬奎斯耐心跟記者解釋。電臺記者的採訪通常都被馬奎斯拒絕,那位記者也同樣吃瞭閉門羹,不過馬奎斯也會稍加安撫,說句「孩子,我愛你」。
馬奎斯於二〇一四年與世長辭,人們委婉地以「健康日益惡化」,描述他生前最後幾年的身體狀況。為瞭敬悼大師,我展讀瞭一篇他早期的短篇小說〈最美的波臣〉(“El ahogado más hermoso del mundo”, 1968 [“The Handsomest Drowned Man in the World”])。那是一篇絕妙的寓言,有關藝術如何提升最平凡無奇的生命,我認為是他的最佳作品之一。在訪談中我曾經把這個感想告訴他,我想那也是他唯一大感詫異的一次。他告訴我,「但那不過是個寫給孩子看的故事」。
新墨西哥市那次訪問的第二天傍晚,他把我們送到附近一間餐廳。他告訴我們,那裡的食物不怎麼樣,不過這頓飯你們會吃得很開心。餐廳深邃幽黑一如洞穴,光線則來自牆上的火炬和桌上的蠟燭。侍者忙而不亂,七手八腳之中自有和諧的默契,而銀質餐具多到我不曉得該怎麼派上用場。侍者在我們桌邊炙烤柳橙,在火焰上快速轉動著,用來調配柳橙咖啡。我計畫中的專訪已經大功告成,我的感覺有點輕飄飄的,輕到差不多足以懸浮在半空中。那感覺就好像身處馬奎斯的故事之中,由大師親自把我帶進那裡──雖然餐廳的食物真的如他所說,還真不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