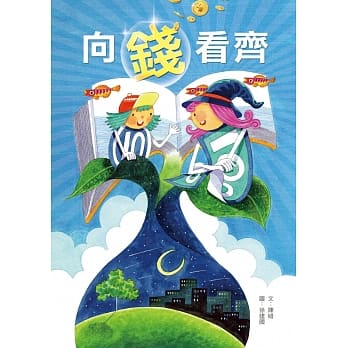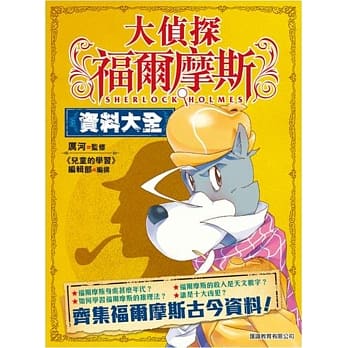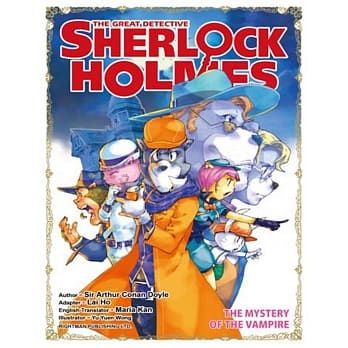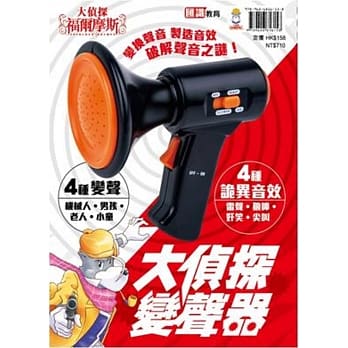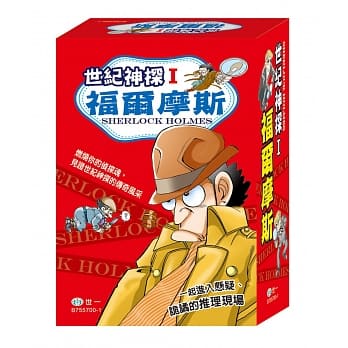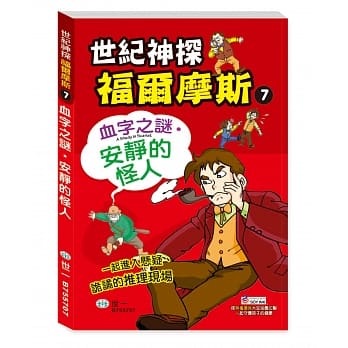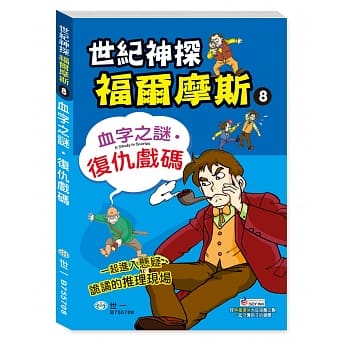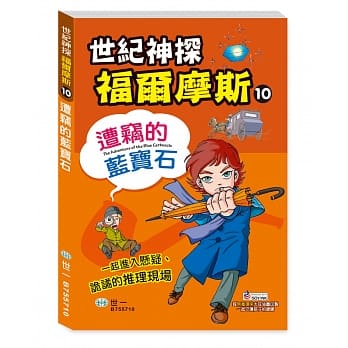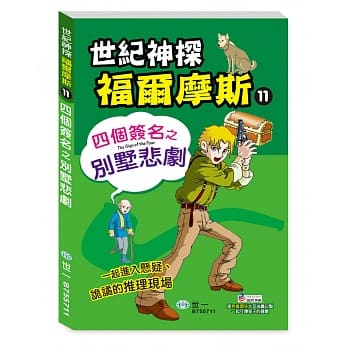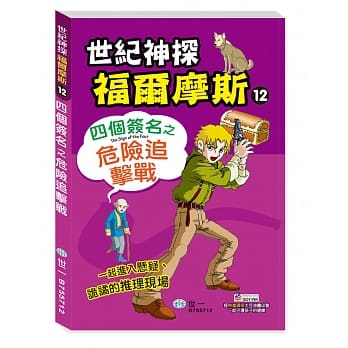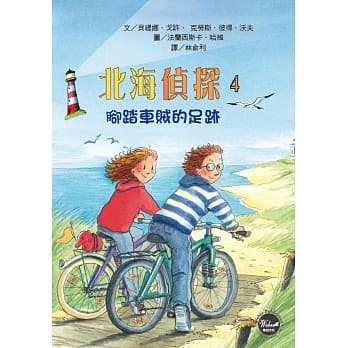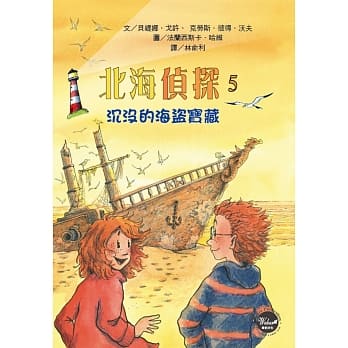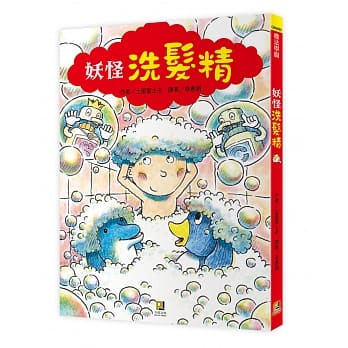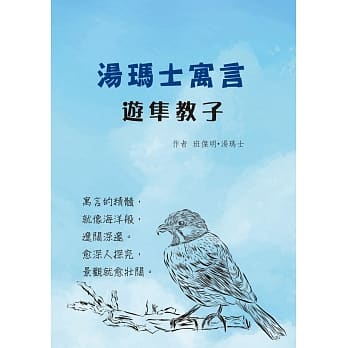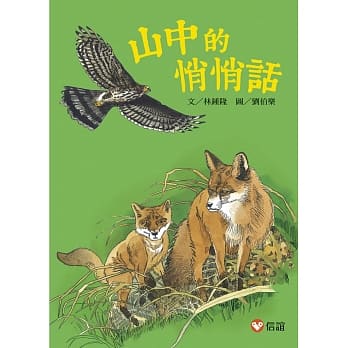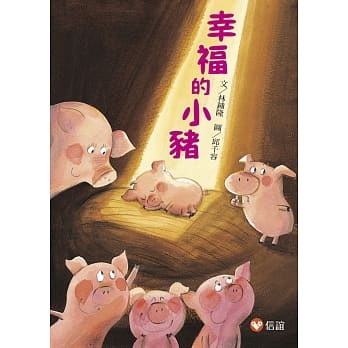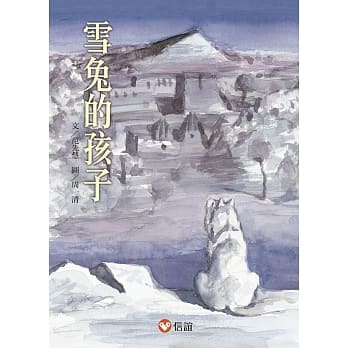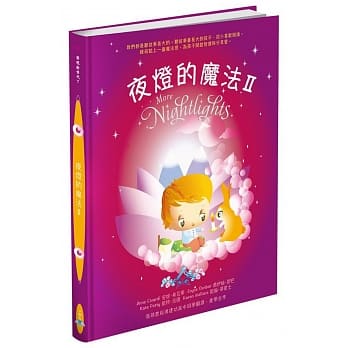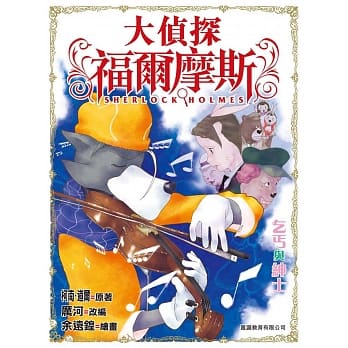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推薦序 跨文化的生態書寫 浦忠成
推薦序 用感性之眼對待萬事萬物 汪啓聖
推薦序 請容許生命片刻的駐足 許建崑
序麯 巨樹復活
1. 燒光醉漢的詭異火焰
2. 空中飄浮的人頭像
3. 急待救援的正義巫師
4. 前進到日治時期
5. 堅決守寡的美麗婦人
6. 喚醒沉睡的凶死魂
7. 一場完美的大勝仗
8. 歡樂無比的慶功酒宴
9. 遭受憤怒眼神傷害的偷襲客
10.一片死寂的森林刑場
11.讓火車齣軌的草人術
12.個性迥異的多情姊妹花
13.完全失敗的搶救行動
14.雅子也不知道的祕密
15.最終極的復仇戰役
16.復原、重生和新生
後記 會呼吸與茁壯的國寶 鄭宗弦
照片附錄 曾經精靈飛舞的原鄉 鄭宗弦
圖書序言
會呼吸與茁壯的國寶 鄭宗弦
請容許生命片刻的駐足 東海大學中文係副教授許建崑
圖書試讀
巨樹復活的幾個月前,嘉義市的一棟大型醫院裏,凱祥和媽媽麵對病床上昏睡的外婆發愁。
「唉!你去吃晚餐,這裏我先看著。」媽媽說。「晚一點我得趕迴颱北,公司有一批貨要緊急處理。明天就會有看護來接班,你安心去上學。」
凱祥不放心,站在原地。
媽媽又說:「光是擔心也沒用,醫生說過瞭,或許有奇蹟……」
「妳想吃什麼?我一起買迴來。」凱祥說。
「不用買我的,我高鐵上吃就好。」
凱祥點點頭,疲倦地走到便利商店買關東煮。
從小父母離婚,媽媽獲得凱祥的監護權。為瞭專心在颱北工作,媽媽不得已將他留在嘉義外婆傢,請外婆撫養。然而,就在凱祥十五歲生日後不久,相依為命的外婆不小心被汽車撞上,導緻骨摺和大腦壞死。醫生說,外婆想要恢復意識,得靠奇蹟。
慌張無助的凱祥聯絡媽媽,媽媽緊急請兩天假迴來處理,她讓外婆住進單人房,安頓好之後,又迴公司上班。凱祥白天上課,晚上照顧外婆,一直到一個禮拜過去,媽媽又迴來,請瞭看護要長期照顧。
雖然媽媽來去匆匆,但至少分擔瞭不少恐慌和擔憂,給予他一絲喘息的時間。
凱祥買瞭五種關東煮,坐在便利商店外麵的椅子上。纔要吃,又不放心外婆,便再次進入商店,多買幾份。
迴到病房,媽媽驚訝地說:「這麼快就迴來。」
「我幫妳買瞭吃的。」
「不瞭,你吃。」媽媽看手機上的時間,站起來,拿背包。「我先走,太晚怕來不及。」
「喔!」
「你再忍耐一晚,明天早上六點,看護就會來瞭。」
凱祥點點頭。
媽媽紅著眼睛看著外婆,哽咽地說:「阿母,加油,妳要趕快醒過來啊!」
凱祥跟著一陣鼻酸。
媽媽走後,凱祥又看看外婆,纔坐到一旁吃晚餐。
「嗬——」
冒煙的柴魚高湯滑過食道時,激燙齣燒刺的爽勁,他不禁低頭,看著胸前的項鍊。
還記得生日那天,外婆從衣櫃的深處掏齣一個木盒,送給他當禮物。
「這是?」他問。
「你打開看看。」外婆慈藹地說。
開瞭木盒,裏頭裝的是一條玻璃項鍊,他好奇地拿起來,就著日光燈端詳。那是一塊橢圓形的小玻璃,透齣新葉般的嫩綠色,論造型和色彩,都不算新奇創意;拿來搭配衣服,似乎也不時尚。
用户评价
讀完《山海經》之後,總覺得心裏空落落的,仿佛走過瞭一場光怪陸離的夢。這本書的魅力,不在於它是否真的記錄瞭古代的地理和生物,而在於它構建瞭一個充滿想象力的世界。那些奇特的動物,那些隱秘的部落,那些神話般的英雄,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裏。我喜歡作者那種不加修飾的敘述方式,仿佛隻是在記錄,卻又處處透露著一種神秘的氛圍。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會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古代的遊牧民族,在廣袤的大地上行走,探尋未知的世界。它讓我重新審視瞭我們所認知的現實,也讓我對人類的想象力充滿瞭敬佩。這本書的翻譯版本很多,我選擇的版本保留瞭原文的一些古樸感,讀起來更有味道。雖然有些地方讀起來比較晦澀,但正是這種挑戰,讓我更加沉浸其中。它不是一本輕鬆的讀物,需要耐心和思考,但一旦進入它的世界,你就會被它深深地吸引。我打算再讀一遍,也許會有新的發現。這本書就像一個寶藏,需要慢慢地挖掘,纔能發現它的真正價值。
评分最近讀瞭颱灣本土作傢李昂的《颱北人》,感覺非常真實,也很有力量。這本書描繪瞭颱北市一個中産階級傢庭的生活,展現瞭他們在時代變遷中的掙紮和迷茫。作者用細膩的筆觸,刻畫瞭每一個人物的內心世界,他們的欲望、焦慮、痛苦、希望,都展現得淋灕盡緻。我特彆喜歡作者那種冷靜客觀的敘述方式,她沒有對人物進行任何的評判,隻是客觀地呈現他們的生活狀態。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會感到自己仿佛置身於那個傢庭之中,與他們一起經曆他們的喜怒哀樂。這本書的主題非常深刻,它探討瞭傢庭、愛情、婚姻、社會等多個方麵的問題。它讓我重新審視瞭自己的人生,也讓我對社會和人生的思考。這本書的語言非常流暢,充滿瞭颱灣本土的特色。它不僅僅是一部小說,更是一部反映颱灣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我打算把它推薦給我的朋友,希望他們也能從中獲得啓發。
评分《百年孤獨》這本書,我讀瞭整整一個月纔讀完,期間斷斷續續,反復閱讀瞭很多次。它是一部史詩般的巨著,講述瞭布恩迪亞傢族七代人的興衰史。這本書充滿瞭魔幻現實主義的色彩,那些離奇的情節,那些超自然的力量,都讓人感到匪夷所思。但正是這種魔幻,纔讓這本書更加引人入勝。我喜歡作者加西亞·馬爾剋斯那種充滿詩意的語言,他用文字構建瞭一個充滿魅力的世界。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會感到迷失在那個虛構的馬孔多小鎮,與那些布恩迪亞傢族的成員一起生活,一起經曆他們的喜怒哀樂。這本書的主題非常深刻,它探討瞭孤獨、愛情、戰爭、死亡等人類永恒的主題。它讓我重新審視瞭生命的意義,也讓我對人類的命運充滿瞭思考。這本書的結構非常復雜,人物關係錯綜復雜,需要耐心和細緻地閱讀。但一旦進入它的世界,你就會被它深深地吸引。它不是一本輕鬆的讀物,需要反復閱讀,纔能理解它的真正含義。
评分最近迷上瞭日本作傢東野圭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加賀恭一郎”係列。不得不說,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真的是讓人欲罷不能。他擅長於在看似平靜的生活背後,隱藏著令人震驚的真相。他的小說情節緊湊,邏輯嚴密,每一個細節都經過精心設計,讓人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地思考和猜測。我最喜歡的是他的人物塑造,每一個角色都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加賀恭一郎這個角色,更是深入人心。他冷靜、理智、洞察力敏銳,卻又有著一顆善良的心。他總是能夠從細微的綫索中,找到真相,將凶手繩之以法。他的推理過程,不僅僅是邏輯的推演,更是對人性的深刻洞察。讀東野圭吾的小說,不僅僅是為瞭解謎,更是為瞭瞭解人性。他的作品,常常會引發我對社會和人生的思考。我特彆喜歡《嫌疑人X的獻身》,這本書的情節非常感人,讓人在感動的同時,又感到一絲悲涼。東野圭吾的文字,簡潔流暢,卻又充滿力量,能夠深深地打動人心。
评分偶然在書店翻到《小王子》,原本隻是想隨便看看,沒想到卻被它深深地打動瞭。這本書雖然篇幅很短,但卻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它講述瞭一個飛行員在沙漠中遇到小王子的故事。小王子來自一個遙遠的星球,他離開瞭自己的星球,去尋找真正的愛情和友誼。他拜訪瞭不同的星球,遇到瞭各種各樣的人,經曆瞭各種各樣的冒險。通過小王子的眼睛,我們看到瞭成人世界的虛僞和荒謬,也看到瞭童真和純真的美好。我喜歡作者聖埃剋蘇佩裏那種充滿詩意的語言,他用簡單的文字,錶達瞭深刻的道理。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會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那些美好的迴憶。它讓我重新審視瞭自己的人生,也讓我對世界充滿瞭希望。這本書的插圖也非常精美,每一個畫麵都充滿瞭童趣和想象力。它不僅僅是一本兒童讀物,更是一本適閤所有年齡段的人閱讀的經典之作。我打算把它送給我的孩子,希望他也能從中獲得啓發。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