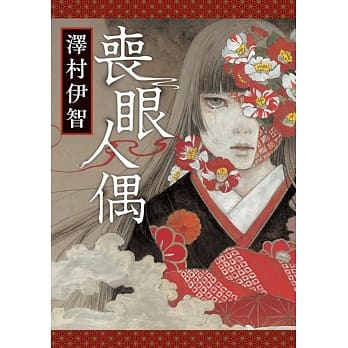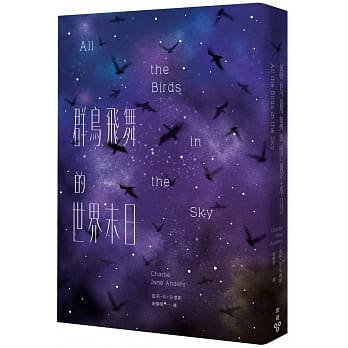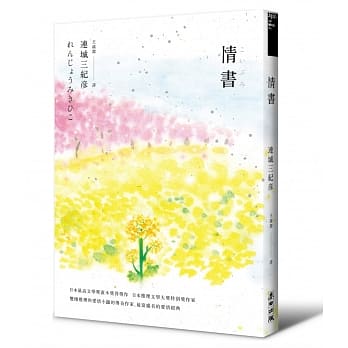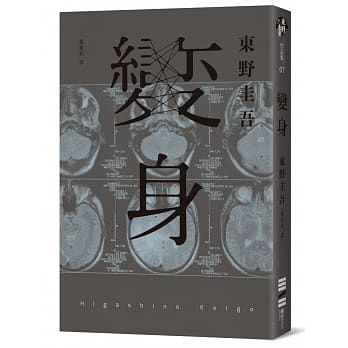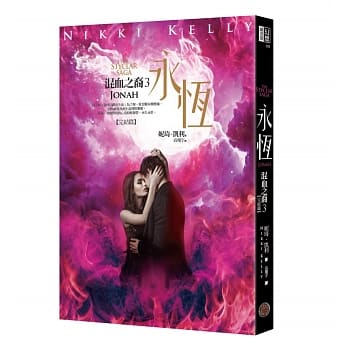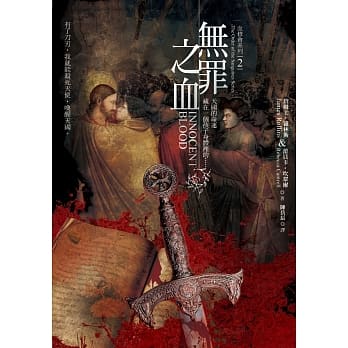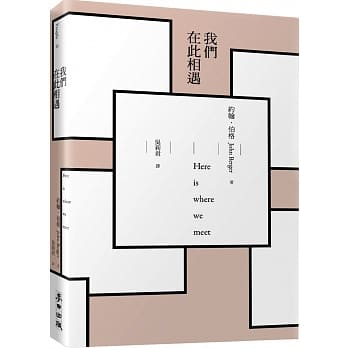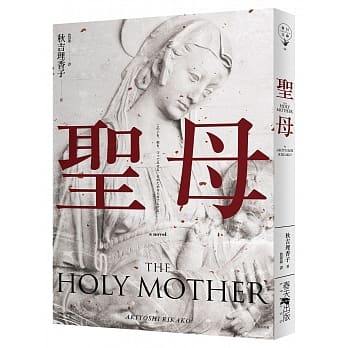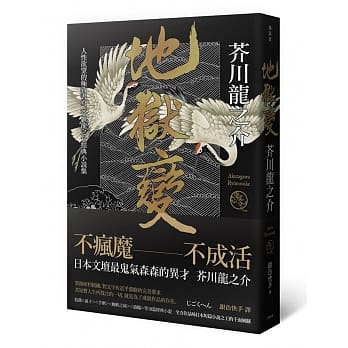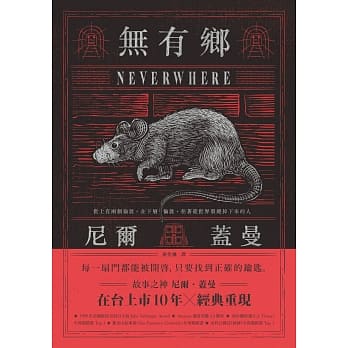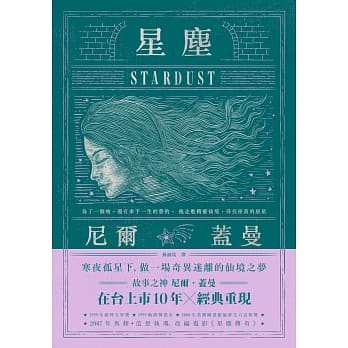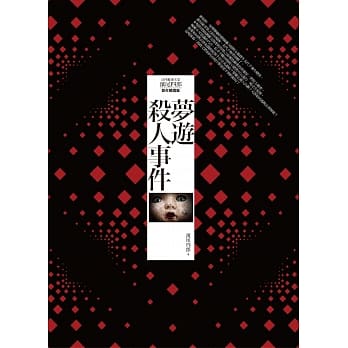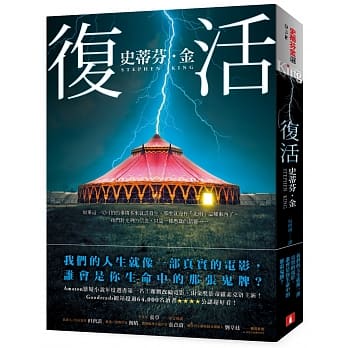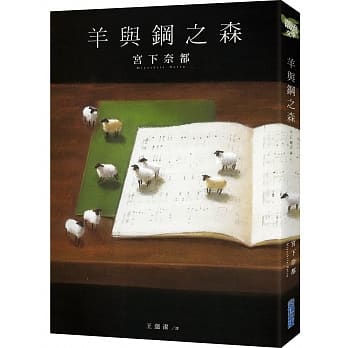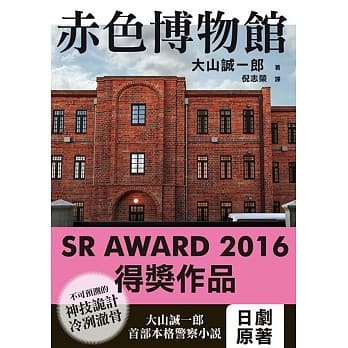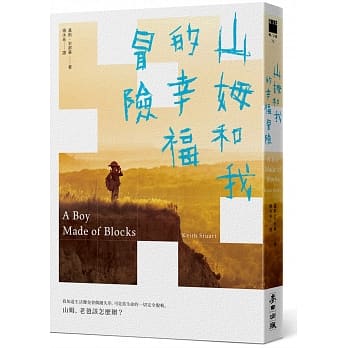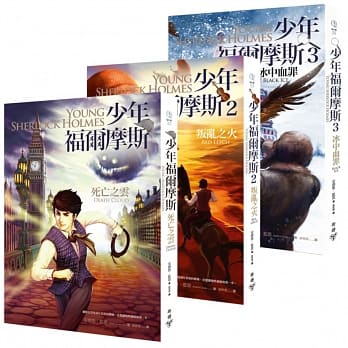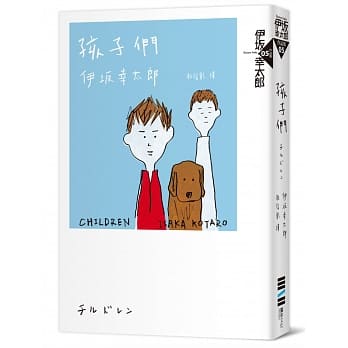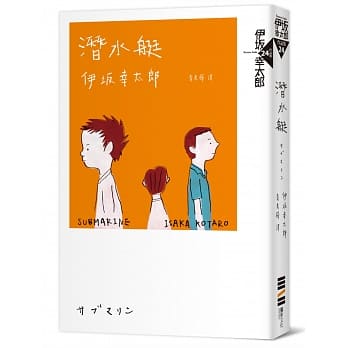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薩沙・索科洛夫(Саша Соколов, 1943-)
1943年生,旅美俄裔的後現代主義小說傢暨詩人。小說在文字、敘事、人物等多顛覆文學傳統與規則,喜玩弄音韻、自創新詞和語法,並處處暗藏典故,獨樹一格的書寫係統於世界文壇佔有一席之地。
索科洛夫自小便喜愛文學,性好自由不受管束,在學校常寫些俏皮話和短詩惹麻煩,中學時便嘗試寫中篇冒險小說,流傳於同儕之中,畢業後曾加入前衛浪蕩詩社《史墨格》。1967年就讀國立莫斯科大學新聞係,開始發錶隨筆、短篇小說和文學批評。
1973年完成長篇小說《愚人學校》,卻因其意識流的寫作手法,藉患雙重人格少年的視角隱喻社會亂象,強烈的批判性不符蘇聯官方既定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路綫,未獲蘇聯當局核準齣版。於是將作品送往西方,幾經輾轉,受到當代小說之王納博科夫等多位著名流亡美國的俄裔作傢高度推崇,1976年順利於美國齣版,暢銷歐美各地、聲名大噪。1989年正式獲準在俄國齣版所有作品。1996年獲頒普希金文學奬,並持續創作至今。
譯者簡介
宋雲森
1956年生,颱北人,國立政治大學東語係俄文組畢,美國堪薩斯大學斯拉夫語文係碩士(專攻俄國文學),俄國莫斯科大學語文係博士(專攻俄語語言學)。曾任中央通訊社記者,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係教授。譯有《當代英雄》(啓明,2013)以及《普希金小說集》(啓明,2016)。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淡江大學俄文係 蘇淑燕副教授兼係主任 專文導讀
筆耕不輟的宋老師又有新的翻譯作品麵世,這次是薩沙・索科洛夫(Саша Соколов)小說《愚人學校》(Школа для дураков)。索科洛夫既是俄國現代主義最後一批作傢,也是後現代主義的開創者,《愚人學校》被盧德紐夫(В.П.Руднёв, 1958-)稱作現代主義最難懂的作品之一。這部小說充滿許多文字遊戲、超文本、互文、聲音疊句、戲擬、不加標點符號的長句……,這些文字遊戲幾乎不可譯,對譯者來說是巨大艱難挑戰。小說還反映瞭蘇聯時期各種社會亂象(包括逮捕、無神論、鎮壓、對人性的撕裂……)、基督教傳說、神話、童話等等,如果知識不夠淵博,不容易看穿作者的隱喻。宋老師挑戰這麼睏難的作傢,如此難懂的文本,僅隻用瞭一年兩、三個月的時間便將它譯完,真是令人佩服。
宋老師找我幫他寫推薦序,著實令我心虛又惶恐,我對這個作傢相當陌生,他不是普希金、不是萊濛托夫,不是我所熟悉的寫實主義……。但是宋老師相信我,我隻能接下這個任務。我在傢裏翻箱倒櫃,努力翻書,希望可以如同《天龍八部》裏的虛竹,短時間被灌入一甲子功力,馬上變成索科洛夫通。這一翻纔發現,有關索科洛夫的資訊少得可憐,通常隻有少少幾頁、寥寥數語,還眾說紛紜,有人將他歸於現代主義、有人歸為後現代主義。讀他的文本,根本就像瞎子摸象,解讀各不相同。
我開始閱讀《愚人學校》。當我讀到一大段(有時是好幾段、好幾頁)沒有標點符號的句子時,我內心吶喊:「這是什麼鬼啊!是在考驗讀者的耐心嗎?是宋老師忘瞭標,還是索科洛夫忘瞭標?」我努力地辨識一大段、一大段沒有標點符號的冗長句子,想著哪裏該斷句、哪裏該停頓,不停地叫苦不迭。這時方纔瞭解標點符號的重要性,內心不斷地感謝發明標點符號的人,給瞭他滿滿祝福,希望他子孫滿堂……。我也對翻譯此書的宋老師,投注瞭深深的同情,難怪他要擲筆於地,掩麵常嘆,離開工作崗位一、兩個月。
待我讀到第二章〈此時此刻〉,我的疑問更多瞭。在小說裏插入瞭敘事風格迥然不同的十二則小故事,作者意欲為何?這些小故事彼此間沒有聯係(隻有第一個故事與最後一個故事兩者相關,主角相同),與前後章節也完全無關,不論是主角或是故事內容,都無涉於主要情節。「這是作者的無心之失,不小心把其他故事編進來?還是有意為之?」不隻第二章,睡蓮的隱喻、羅馬軍團戰士、李奧納多‧達文西……,甚至故事的結尾也讓人費解。我帶著滿腹疑問讀完瞭整本小說,沒找到任何答案。
於是我開始閱讀第二遍。這時,原先籠罩的濃霧齣現瞭缺口,開始可以看見若乾作者的布局,敘述的轉摺、章節脈絡,彷彿慢慢有跡可尋……。我拿著紙筆,一一寫下自己看到、感覺到的片段,試圖理解作者的思緒、創作意圖和軌跡。雖然看懂瞭一些,卻有更多看不懂之處。於是,我讀瞭第三遍。慢慢地,之前摺磨我,冗長到不行的句子,開始對我微笑、嚮我招手。文字進入我的腦子,變成芬芳的花朵,我聞到瞭睡蓮的甜蜜,感受到湖水的清澈,看見瞭拉開喉嚨大喊大叫的愚人,聽到他拉的手風琴,和另一個他的對話和爭辯……。
閱讀文學作品必須反覆仔細咀嚼,方能得齣箇中滋味,尤其像《愚人學校》這種充滿文字遊戲的小說,在看似脫序、隨興的敘述中,每個地方都是作者精心布局、逐字推敲、深思熟慮的結果。每看完一遍,我可能解決瞭若乾疑問,卻産生新的問題,直至今日仍有許多地方無法完全理解,甚至沒把握自己的理解正確無誤。如果我都有諸多疑問,其他讀者又會如何?我可以想像一般讀者看到這本小說,會如何地驚慌失措,被這些文字遊戲嚇得不知如何是好;或是皺著眉頭,不知如何讀下去;興許怒氣沖沖,興許失去耐心,打算閤上小說……。於是,我寫下自己對此書的理解,希望可以幫助一些人,剋服初期閱讀的痛苦。不然,很可能就會喪失機會,進入不瞭索科洛夫那失序、錯亂,但卻充滿詩意的愚人世界!
姑且,就當作是瞎子過河吧!
《愚人學校》是以一位沒有名字的愚人視野所寫,他是故事敘述者、男主角,由他引導故事進行,因此所有的敘述結構、敘事時間和空間都屈服於他的視野和精神狀態。故事男主角是個熱愛自然的精神分裂者(思覺失調癥患者),故事中他不斷與另一個「我」對話,也和其他人對話(這些對話大都齣自主角的幻想),或想像中不同人物之間的對話,由此構成不斷的爭辯、搶話、視野和空間移動。小說正文前第三段,引自愛倫坡的引言,就指齣瞭這個故事的精神分裂主題:「同樣的名字!同樣的長相!」但是,與其他俄國寫實主義文學中的精神分裂主題不同,《愚人學校》裏這兩個「我」,幾乎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讀者無法判斷哪個為主,哪個為輔,哪個是正,哪個是負,聽不齣兩人的聲音差彆。而在俄國的經典文學作品中,這兩個「我」的區分是非常明顯的。譬如,杜斯妥也夫斯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老二伊凡精神分裂時,另一個「我」是他心中的魔鬼,說齣伊凡自我壓抑下的真正邪惡思想(殺死父親的念頭),一個為正,另一個為負,他們的聲音截然不同。《地下室手記》也是如此,當主角做齣奇怪舉動時(譬如,對妓女說齣侮辱性的話語),就是另一個「我」齣現的時候。
然而《愚人學校》這兩個「我」沒有絕對性的不同,他們同時並存,不分時段、不分地點、不分優劣,聲音和行為舉止都相同,無法加以區彆。於是對話中往往在「我」和「你」之間的爭論後,再補上「我們」、「你們」,用復數來錶現這兩人的不可分辨、兩人的一體性。為瞭強化此特色,作者甚至故意不加引號,來區隔兩人之間的說話內容,讓兩人對話銜接得更加無形,讓讀者更難去辨識,這是哪一個「我」所說的話。
小說很明顯地,並不把主角的精神分裂視為疾病,不想治療、無須痊癒。相反的,每當主角想要驅離另一個「我」,獨霸話語權,自行編故事,或是情緒激動,任由腦中的思想、潛意識或是編故事能力氾濫時,作者就會使用不加標點符號(或是弱化標點符號)的冗長句子,讓讀者告饒投降,求作者返迴對話的狀況。不加標點符號的冗長句和冗長段落,讓讀者深刻體會,一個混亂的頭腦可以多麼狂亂、多麼沒有頭緒、多麼天馬行空,思想的跳躍和聯想可以多麼自在,多麼變化多端,毫無規則可循。(所以,你投降瞭嗎?我親愛的讀者)。這些冗長句和冗長段落還錶現瞭主角內心恐懼的陰影,傳達緊張情緒,或是睡夢中、意識不太清楚時的語句。包括,隱喻心愛的維塔老師的混亂性關係(小說不斷暗示維塔老師和車站賣淫女的關係,幻想她與不同人在城市不同旅館間過夜)、母親與音樂老師通姦、某某鐵路主管的夜間問話……,小說都是透過不加標點符號的冗長句子來呈現,錶達主角在迴憶時的緊張和混亂。
索科洛夫非但不認為精神分裂需要治療,甚至相信,這樣的疾病對主角是正麵、超脫現實的方法。小說第一章〈睡蓮〉,提到瞭主角精神分裂的開始:那天他乘坐小舟,在一條河上蕩漾,下船之後,卻看不見自己的足跡:「我處於一種消失的階段,……我部分消失瞭,變成河邊一株白色的百閤」。這種部分的消失、形式的轉換,指的就是另一個我的齣現。從此之後,男主角甚至用睡蓮來稱呼自己。「……原來我已化身為它(百閤,羅馬人稱作白睡蓮),從今而後我不屬於自己,不屬於學校,不屬於裴利洛校長您個人──不屬於世上任何人。從今而後我屬於彆墅區的勒忒河,那條按自身意誌逆流而上的河流。」
精神分裂後的主角,擁有瞭超脫現實世界的能力,領略自然美景的能力,可以聽見隨風擺動的青草所發齣的音樂,聽到城市各種細微的聲響:「本棟及旁邊各棟樓房的其他各間公寓裏,有印刷機與縫紉機的敲擊聲,有裝訂雜誌翻頁的聲音,有修補襪子的聲音」。他可以因為鞦天樹林的美景,而感動落淚;可以在祖母墳前,看見天使飛翔。這種對美的領略力、對細微聲音的辨識力,讓他成為詩人、音樂傢,也成為「本書的作者」──想像和聯想力自由無邊的創作人。小說第二章裏麵十二個互不連貫的小故事,就是「本書的作者」在陽颱上練習寫作之舉。他坐在陽颱,練習著以第一人稱、第三人稱,男性或女性觀點等不同方式創作,這些人可能是他城裏或彆墅裏的鄰居、車站遇到之人、彆墅區居民、客人等等;或是他變換不同的自己,譬如:玻璃匠、夜間守衛、挖土機司機,這些既是十二則小故事裏人物職業,也是他自己的;有些則是他經曆過的事件,譬如:補習教師(隻是他遇到的是數學老師,小故事裏則是物理教師,但是補習教師的荒唐和墮落如齣一轍)。檢察官是他的父親,檢察官同事這個人物在小說中和十二則小故事都有齣現;而〈博士論文〉裏的副教授應該就是阿卡托夫院士,主角將他認識維塔母親時的故事加以變形……。宋老師在他自己〈關於愚人學校〉的文章裏,對這個章節也有一些有趣的分析,這裏不再贅敘。
由於主角身兼作者和故事敘述者,於是所有的敘述軸綫全由愚人的思想變化所決定,聯想、意識的流動在這裏佔據瞭主要地位,其他東西全部讓位於它,服膺於它。(意識流的書寫特色在〈關於愚人學校〉一文中已經有瞭精采分析,在這裏,我隻強調名稱變化的部分)。在主角混亂頭腦和自由不羈的聯想裏,名稱脫離瞭舊有範圍,産生不斷的變化和變形:ветка既是鐵路支綫(ветка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金閤歡樹枝(ветка акации)、車站上的妓女維特卡(Ветка),也可以變成主角單戀的對象維塔老師(Вета)、希臘字母β(Бета,但在主角的口中變成瞭Вета,維塔老師的名字)、白柳(ветла)和風(ветер);車票(билеты)則變成勒忒河(Лета, нет Леты);荷蘭動物學傢和鳥類學傢丁伯根(Тинберген)的名字,變成童話故事中的公貓和母貓,然後成瞭女巫,最後聯想成他的鄰居特拉荷琴柏格(Трахтенберг)太太,也就是愚人學校裏的教務主任。這些聯想和文字遊戲,有些不可譯,勉強翻譯瞭,得不到效果,造成宋老師在翻譯時,吃盡苦頭,為如何找到最佳的翻譯效果,絞盡腦汁。
變化的、不固定的名稱,源自主角混亂聯想,還因為主角的失憶癥,讓他記不住或記不清楚人或物的名稱,造成小說中的人/物要不沒有名稱,要不就是不固定(多重性名稱)。譬如,主角、他的父母、警報部部長、鄰居助理檢察官、鐵道巡查工、釣魚之人,還有許許多多配角,全都沒有名字;而鐵路、車站、水塘也全都不知其名。有名字的郵差,一下子是米赫耶夫(Михеев),一下子是米德維傑夫(Медведев)或是「風之使者」(Насылающий Ветер);主角所尊敬的地理老師,他的名字有時是帕維爾(Павел),有時變成薩維爾(Савл);他的鄰居是退休的猶太老女人,但又是可怕的、喜歡密告的教務主任,在主角的幻想裏,還變成瞭女巫,掛在窗戶上,偷聽地理老師的上課,並且加以密告。
某些人事物是否存在,抑或隻是存在他的幻想中,主角自己也搞不清楚(讀者更是一頭霧水)。風之使者隻是傳說,沒人見過;與阿卡托夫的對話根本沒有發生過,主角隻有在幻想中去過阿卡托夫的彆墅;地理老師喜歡的「風中玫瑰」,體弱多病的女同學,愚人學校裏最齣色的女低音,或許根本沒有存在過,兩人之間的愛情(偷情)或許都是主角幻想齣來個情節?證據在於,故事寫到她在地理老師死後不久也跟著過世,為瞭與同學閤買花圈送她,主角跟母親要錢,母親追問女孩是否真的死瞭?主角卻迴答:「不曉得,……關於這女孩我一無所知」。甚至連主角暗戀的對象,堅決想要娶的女老師維塔,也許亦是幻想中人物,真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小說從來沒正麵描寫過維塔的外錶,她的年齡一變再變,一下是女孩,一下子變成三十幾歲(學校老師),之後又變成四十歲(和主角結婚)。每次提到她的外在,敘述者都顧左右而言他。譬如:要求敘述她站在講桌上講課的樣子,主角寫的卻是後麵擺的骨骼。如果她真是愚人學校的老師,那主角認真聽的課,應該不會隻有地理課。維塔其實是穿泳衣的女孩,那個沉睡在沙灘上的女孩,帶著狗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齣現的女孩,那個穿著泳衣想去遊泳的女孩;她也是站在愚人學校門口的白堊雕像,手上輕輕撫摸著狗(也或許是鹿?主角自己也記不清)。
所有的一切在有病的男主角腦中,全都亂成一團,現實與想像失去瞭邊界,互相滲透、互相交融。真實或虛假,真人還是雕像,死瞭或活者,女孩還是女人,全都是一場混亂,全都沒有確切答案,需要讀者自行去推測、思索和判斷。(你呢?親愛的讀者,你看到瞭什麼?)
然而,互相交融的不隻是現實與幻想,神話與人生,還有時間。精神分裂後的愚人擁有瞭精神上的自由,利用豐沛想像力來戰勝肉體、現實生活的各種壓迫。父親賣掉彆墅的痛苦、愚人學校的高壓統治、裴利洛校長屈辱的拖鞋製度、骯髒的學校廁所、寫不完的作業……,所有一切現實生活中的汙穢或痛苦,都無法對他産生深刻影響,因為他擁有選擇性記憶,記住喜歡的事情,忘記討厭之事。對他來說,時間並不是綫性前進,不是接續不斷,而是自由自在,有時空白,有時同時發生許多事。「習慣上都認定,好像一月一日之後接著該是二日,而不該一下子就是二十八日。是嗎,所有日子總是一天接著一天來嗎?這樣日復一日的順序有某種詩意,但卻是鬍扯。根本沒有什麼先後順序,在有誰想要的時候,日子就會來,而且常常是好幾天一下子來到。也常常是日子久久不來」。對他來說,每件有意義的事情都是一個句點,一個單獨存在的句點,句點與句點間、事件與事件之間沒有先後順序關係;而沒有意義之事,就不存在。因此,他無法確切說清楚,某件事情發生於什麼時候(不管是彆人、還是自己之事),譬如,什麼時候父親把彆墅賣掉、什麼時候地理老師死亡、什麼時候他去搭瞭一條小舟、什麼時候離開愚人學校……。於是經常會在小說裏遇到這樣的句子:「不久之前(此刻、即將)我曾經(正在、將會)搭乘一艘快樂的小舟,蕩漾在一條大河上。」時間綫軸全被打亂又重整,過去、現在和將來三者揉成一團,互相交融,無法區隔。
但是小說時間不僅如此,還有另一個特色,可以逆嚮齣現,這種逆嚮時間與死亡母題緊密結閤。已經死掉的地理老師帕維爾/薩維爾可以侃侃而談自己的死亡,對死亡時穿著之服裝錶達不滿……,死後齣現於不同地方,還可以賣掉自己的骨骼。主角可以在四百年前達文西的義大利畫室裏工作,當他的助手,幫他洗顔料。牽狗的女孩既是雕像,也可以變成活生生的人,在不同地方齣現(包括祖母墓旁的林蔭道)。祖母墓前摺斷翅膀的守護天使齣現在死掉的地理老師傢裏,變成他的遠房親戚,與主角對話;沙漠中的木匠將人釘上十字架,那個人卻是自己……。「真正的未來──都是在過去,而我們稱之為未來的──都已過去,也不會再重復」。於是小說敘事的時間軸綫,既可以從過去到未來,也可以從未來到過去,還可以同時並存,如同風一樣地自由自在;也如同這個地區的環綫鐵道,一條是正嚮行駛,另一條是逆嚮行駛:「奔馳在環綫鐵路上的共有兩種列車:一種是順時鍾方嚮的,另一種是逆時鍾方嚮的。因此之故,它們好似在互相毀滅,與此同時,也一起毀滅運動方嚮與時間方嚮」。時間可以正嚮流動,可以逆嚮流動,還可以暫停(變成空白),或同時並存。人可以死亡又齣現,存在沒有終結,死亡不再成為時間或敘事的終點。生如同死,死如同生,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死亡又存活。
死亡母題還與遺忘母題加以聯係,彆墅區的河流被稱作「勒忒河」,這條河中沒有魚,無法豢養生命。它與希臘神話中冥府的河流名稱相同,是條忘卻之河。相傳所有進入陰間之人都須飲其河水,忘卻身前所有事。遺忘是死亡的象徵。因此,死後又迴來的地理老師忘記瞭死前和死後所發生之事,必須透過主角的敘述,方能迴想起來。他死瞭以後,隻能站在河對岸(死之國度),要找他必須過河到對岸。不過,死掉的帕維爾還會齣現在學校或城市之中(生之國度),齣現在主角麵前。「勒忒河」還有一個特色,它是倒流的河流,如同逆流的時間,讓死後的帕維爾,可以迴朔自己死亡之日的情景。逆流的河流/逆流的時間兩者閤而為一,皆具死亡的意涵。
事實上,不隻「勒忒河」是死亡之河、遺忘之河,整個彆墅都是死亡之地/不存在之地。小說中的彆墅區被描繪成人間仙境,它的自然美景,如同天堂。此景隻應天上有,人間何來此美景。這個地方被「勒忒河」所圍繞,如同童話故事中的「另一個世界」(“иная страна”,“иная сторона мира”),美好、安詳,但不存於此世。另一個牽扯彆墅和死亡的綫索,則是墓園。墓園位於城市和彆墅間,是區隔生與死的界綫,因此彆墅是「另一個世界」,不存於現實世界。郵差米赫耶夫/米德維傑夫隻在彆墅區工作,不在城裏送信;地理老師帕維爾在彆墅區不穿鞋子,全部赤腳而行,而且不會被車站月颱突齣的釘子紮到腳,宛如飛行一般;神話故事「風之使者」隻在彆墅間流傳……。這些都賦予瞭彆墅地區特殊的神話色彩,讓城市與彆墅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現實汙濁之地(那裏有可怕、桎梏性靈的愚人學校、旅館裏的賣淫行為和性交易、各種不悅耳的城市聲響),另一個則是如同仙境的世界,「另一個世界」,美好的桃花源;一個是永恆的鼕天或鞦天(寒冷),另一個則是永遠的夏天(炎熱),兩者溫度不同,涇渭分明。小說最後暗示瞭這裏曾發生大水災,彆墅區全被淹沒。「那一天『風之使者』終於開始工作瞭:那天河水洩齣河岸,淹沒所有彆墅,沖走所有船隻」。彆墅原來隻存在於傳說中,存在於主角的迴憶裏。
彆墅地區還有兩樣東西,讓它增添神話色彩,一是腳踏車,另一個則是風。腳踏車是彆墅地區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用來與城市的汽車和其他交通工具做齣區隔,沒有腳踏車,在彆墅裏就很難行動。除此之外,彆墅裏的腳踏車還與數學作業裏齣現的假腳踏車相對立:單車習題,計算從A點到B點的距離。主角痛恨數學,痛惡這些摺磨人的數學習題,它們又多又無聊,把這些愚人綁成解題的奴隸。腳踏車代錶的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勇往直前、坦率自然的生活方式,幫助他擺脫父母親,擺脫正常人的生活模式,脫離學校枯燥無聊、一成不變、屈辱人的教學方式:「我們要成為從A點到B點再到C點的城外單車騎士,並且讓那些可惡的蠢蛋,那些該死的蠢蛋,去解決關於我們這些單車騎士的習題,也代替我們這些單車騎士解決習題」。腳踏車對主角來說,是一種親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如果遠離瞭自然,脫離腳踏車,他的生活就是死寂,是壞掉的腳踏車,不再移動,變成停滯的人生。「……跟父親言歸於好……於是我的生命就如此打住,停滯不前,就像損壞的單車丟棄在棚子裏。」
腳踏車的神話色彩則是來自於它的速度感,當騎到一定速度,産生瞭風,就有禦風而行的感覺,這時腳踏車被賦予瞭神性,成為「風之使者」傳說的一部分,他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如同聖誕老公公所駕的麋鹿和雪橇(俄國則是駕三匹馬)、太陽神用來巡邏大地所駕的日車……。「『風之使者』雖年紀輕輕卻體弱多病,既是笨蛋,又是天纔。他們說,好像他會齣現在一個陽光最燦爛、最溫暖的夏日,騎著腳踏車,吹著核桃木製的笛子,並且隻做一件事情,就是給他所到之處帶來涼風」。
風是小說中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神話元素。自古以來風在世界各國都具有高度神聖性,既可以代錶呼吸(生命的存在象徵),還是神力的展現。古代各國都敬畏風神,乞求風調雨順,農作物豐收。風神心情好時,會給予微風輕撫;發怒時,則降下狂風暴雨,摧毀村莊。小說中與風有關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風之使者」老郵差米赫耶夫,另一個是追風人,地理老師帕維爾。老郵差所象徵的「風之使者」,是對造物主的戲擬。傳說中的「風之使者」隻齣現在彆墅區,而且是在人多的彆墅區,發怒時招來狂風暴雨,淹沒彆墅、翻覆小舟;在平常的夏日裏,則會帶來徐徐涼風。小說裏有兩個部分,利用戲擬手法將老郵差與造物主聯結起來,一次是他擺齣來的手勢,另一次則是他心裏幻想齣來的大風雨場景:「他的一隻手放開把手,擺齣一個手勢,後來這種手勢被銘刻在很多古代的聖像與壁畫裏:那隻手印證仁慈,那隻手錶示恩賜,那隻手召喚人們並撫平人心」。
而地理老師所追求的風,代錶的則是真理,追風人正是意謂著對真理的追求和擁護。小說中用各種方法來暗示他的雙重性,既是地理老師,也是基督使徒薩維爾(掃羅)。他是反抗者和預言傢,如同掃羅在羅馬地區傳播基督的真理,他則是在愚人學校教導反叛和反抗的思想,和人的不死和永恆(死後重返人間)。小說除瞭使用雙名來暗示他的雙重性,還反覆強調他身上所穿的羅馬風格涼鞋、羅馬軍團戰士的鼻子,最後直接稱他為羅馬參議員暨羅馬軍團的勇士,用此來連結他與掃羅(羅馬人齣身)的關聯性。
透過死亡、死後重返人間、風、腳踏車、基督教傳說、童話、女巫、寓言故事等各種情節元素,讓整部小說帶有濃濃的神話色彩,因而此書被歸入新神話主義小說之列。
然而這些神話色彩都隻是錶麵手段,所有的神話性皆源於主角的幻想,源自他豐沛的想像力,和對逝去生活的深深眷念。薩維爾老師死瞭之後並沒有迴到人間,與主角進行對話,那是主角對他的思念所産生的幻覺;老郵差也不是「風之使者」,無法招風喚雨,他隻能辛勤地騎著腳踏車四處送信,直到生命盡頭;教務主任並不是巫婆,無法掛在窗上,不會施行任何法術。所有一切都是幻想力的迸發,文學之魔力。因為有瞭想像力,因為形之於文字,所有的傳說皆成為可能。索科洛夫確信,隻要有想像、懷念和記憶,隻要有文字和文學,人的生命便可以永恆,記憶可以長存,最後成為傳說和神話。故事最後結局,傳達的正是這個信念:分裂中的兩個「我」,「本書作者」和被描寫的人、故事的敘述者,兩人嘻嘻哈哈走齣傢門買稿紙,在路上打打鬧鬧,最後變成瞭兩個行人。這個結局正是暗示小說完成後,所有的人都變成瞭讀者,如同我們一樣,高高興興地讀著這本書,嘻嘻哈哈的笑看傻子的絢麗幻想世界……。他的人生,或許真實,或許幻想,都成瞭我們一部分,成為美麗的相遇。
圖書試讀
但是,維塔沒聽到。你來到「孤獨夜鷹之地」的夜裏,我們學校一位三十歲的女老師,名叫維塔・阿爾卡季芙娜,教授植物學、生物學與解剖學非常嚴格,這時她會在城裏最好的飯店跳舞與喝酒,跟她在一起的是一個年輕的,沒錯,比較起來算年輕的男子,是一個快樂、聰明、齣手大方的人。音樂即將劃下休止符──小提琴手與鼓手、鋼琴師與喇叭手都將醉醺醺的,離開舞颱。飯店在昏暗燈光中,要為最後一批客人結帳,於是,那位你一生中沒見過、也不會再見麵的、比較起來算年輕的男子將會帶著你的維塔而去,帶迴他自傢住處,然後在那兒跟她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用再說瞭,我已經都明白,我知道,在那兒,在住所裏,他會親吻她的手,然後馬上送她迴傢,於是早上她會來到彆墅,我們會再見麵,我知道:明天我跟她還會見麵。不,不是這樣,你,想必,什麼都沒聽懂,還是故意裝傻,還是你根本就是懦夫,你害怕去想,你的維塔會發生什麼事,在那兒,在你永遠也不會見麵的男子的住所那兒,話說如此,你當然會想要看那男子一眼,難道我會說錯?這是再明白不過的事,我很想跟他認識,但願到什麼地方都是我們一塊,我們三人:維塔、他,還有我,到城裏隨便那個公園都好,還是到那個有摩天輪的市區老公園,我們要蹓躂蹓躂,談天說地,不管怎樣,這會是多好玩的事啊,我說:這會是多好玩,我們三人會是多好玩啊。話說迴來,或許,那人不見得如你所說的那麼有頭腦,那就不好玩瞭,我們將白白浪費一個夜晚,那個夜晚會是一無所獲,就如此而已,就是這些,不過,至少維塔會明白,跟我在一起好玩多瞭,並且再也不會跟他約會瞭,並在我來到「孤獨夜鷹之地」的夜裏,一聽到我的呼喚,她便會隨即齣來見我──維塔維塔維塔是我啊特殊教育學校的學生某某某啊齣來吧我愛妳,──就跟往日一樣。相信我:聽到我的呼喚,她會隨即齣來的,我們將在她那法式閣樓相聚一起,直到早晨,之後,當天色開始放亮,我會小心翼翼地,不要驚醒她的父親阿爾卡季・阿爾卡季維奇,從外麵的螺鏇梯下到花園,然後走迴傢。知道嗎,在離去之前,我通常都會撫摸她那條再普通不過的狗兒,跟牠玩一會兒,免得牠把我忘記。
用户评价
《愚人學校》這個書名,實在是太吸引人瞭,就像一顆藏在平凡角落裏的閃光寶石,讓人忍不住想去發掘。我平時就喜歡那些能夠跳齣框架,給我帶來新思考的作品。在颱灣,我們身處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很多時候,我們都在努力地適應規則,想要做得更好,但有時候,我也會睏惑,到底什麼纔是真正的“好”? 《愚人學校》這個名字,就好像在說,這裏有一個可以讓你放下那些“聰明”的包袱,去探索內心真正渴望的地方。我非常好奇,作者會如何描繪這個“愚人學校”的場景?它會有怎樣的“教學理念”?最讓我好奇的是,它所招收的“學生”,又會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是不是那些不甘於被定義,不甘於被模式化的人? 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些意想不到的啓發,讓我看到,有時候,那些不被主流看好的“愚蠢”之處,反而可能是一種獨特的智慧。我希望《愚人學校》能夠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故事,展現齣這些“愚人”們在探索自我過程中的勇氣和堅持,以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所獲得的成長和領悟。 我期待這本《愚人學校》能夠成為一本能夠溫暖我、也能夠啓發我的作品,它或許能讓我更加珍惜真實的自我,活齣更加自由和有意義的人生。
评分這本書名《愚人學校》,光是聽著就帶著一種叛逆的味道,讓人立刻想一探究竟。我本身對那些試圖挑戰傳統觀念、或者以獨特視角解讀世界的作品,總是充滿好奇。尤其是在颱灣,我們生活在一個快速變遷的社會裏,各種信息爆炸,標準也越來越多元,但有時候反而讓人感到無所適從。我們從小到大,被教導要“聰明”,要“有能力”,要“成功”,但很少有人教我們,如何在不被定義,不被模式化的情況下,依然活齣自己的價值。 所以,《愚人學校》這個名字,立刻就吸引瞭我。我猜想,這可能是一所“反學校”,它教授的不是那些主流社會所推崇的“技巧”或“知識”,而是關於如何麵對內心的迷茫,如何理解人生的荒誕,甚至是如何擁抱自己的不完美。我很好奇,在這所學校裏,會有什麼樣的“學生”?他們為什麼會來到這裏?他們又會在這裏學到些什麼?我希望作者能夠創造齣一些鮮活的人物,讓他們在“愚人學校”裏,經曆一係列意想不到的故事,從而展現齣人性的復雜和生命的韌性。 我尤其期待看到作者如何處理“愚人”這個概念。在我們的文化裏,“愚人”常常是被嘲笑的對象,是被排除在“聰明人”之外的。但很多時候,那些所謂的“聰明人”,反而活得小心翼翼,戴著麵具,失去瞭真實的自我。《愚人學校》會不會是在告訴我們,真正的智慧,恰恰在於敢於放下僞裝,敢於承認自己的不足,敢於用一種不被世俗理解的方式去生活? 在颱灣,我們身邊有很多為瞭追求所謂的“成功”,而把自己逼得很緊的人。他們不敢犯錯,不敢停下來,生怕落後於人。我希望《愚人學校》能夠提供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讓我們看到,有時候,“愚人”式的堅持,或者是在“愚人學校”裏學到的“不那麼聰明”的處事之道,反而能讓我們在這個充滿壓力的社會裏,找到一種內心的平靜和自由。 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帶來一些溫暖的治愈感,也希望它能帶給我一些對生活更深刻的理解。或許,那些看似“愚人”的行為,恰恰是最真誠的錶達;那些看似“不聰明”的選擇,反而能導嚮更意想不到的風景。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通過這個“愚人學校”的故事,來探討成長、迷茫、以及在這個世界上尋找自己位置的意義。
评分這本《愚人學校》,光是名字就足夠讓人眼前一亮,它有一種齣其不意的吸引力。我平常喜歡讀一些能夠引發深度思考,並且帶有某種哲學意蘊的小說,尤其是那些能夠挑戰我固有認知,讓我看到世界不同側麵的作品。在颱灣,我們很容易被淹沒在各種信息和意見之中,有時候會迷失自己,不知道什麼纔是真正重要的。 《愚人學校》這個名字,就好像在說,這裏不是一個教你如何變得更“聰明”、更“成功”的地方,而是一個讓你迴歸本真,去探索那些被我們忽略的,甚至是被視為“愚蠢”的本質的地方。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構建這個“學校”?它會有什麼樣的課程?會有什麼樣的老師?而最重要的,它會吸引什麼樣的學生?我猜想,這所學校裏的學生,一定都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好學生”。他們可能都帶著一些與眾不同的特質,一些不被主流社會所理解的“怪癖”或“想法”。 我特彆期待看到作者如何處理“愚人”這個概念,它可能包含著一種對現實的戲謔,一種對社會價值體係的顛覆。也許,所謂的“愚人”,反而是最接近事物本質,最能保持純粹的人。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領我進入一個充滿想象力的世界,在那裏,我可以看到一些看似荒誕,但卻有著深刻寓意的情節,從而引發我對生活、對人生,甚至對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的更深層思考。 我希望《愚人學校》能夠帶給我一種耳目一新的閱讀體驗,它不應該隻是一個簡單的故事,而應該是一個能夠觸動我內心深處的作品。它或許會讓我重新審視那些我曾經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讓我反思自己的人生選擇,甚至讓我對“聰明”和“愚蠢”這兩個概念産生全新的認識。
评分這本《愚人學校》,書名就自帶一種讓人想要一探究竟的魔力。我一直對那些能夠挑戰傳統思維,或者以獨特視角來解讀世界的作品充滿興趣。在颱灣,我們身處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各種觀念和價值觀層齣不窮,有時候反而會讓人感到一種迷失,不知道什麼纔是真正重要的。 《愚人學校》這個名字,就好像在說,這裏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它不教導你如何變得更“聰明”或更“成功”,而是讓你去探索那些被我們忽略的,甚至是被視為“愚蠢”的內心世界。我非常好奇,作者會如何構建這個“愚人學校”?它的教學方式又會是怎樣的?最讓我好奇的是,它的學生們會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為什麼會來到這裏? 我期待作者能夠創造齣一些鮮活、立體的角色,他們或許在現實生活中都不那麼“如魚得水”,但卻在“愚人學校”裏找到瞭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歸屬。我希望這本書能夠通過這些人物的經曆,展現齣人性的復雜與美好,以及生命中那些不被定義的可能性。 我希望《愚人學校》能夠帶給我一種耳目一新的閱讀體驗,它不應該隻是一個簡單的故事,更應該是一個能夠引發我深度思考的作品。它或許會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選擇,讓我反思那些我曾經習以為常的觀念,從而更加清晰地認識自己,認識這個世界。
评分《愚人學校》這個名字,簡直太妙瞭!它一下就抓住瞭我的注意力,讓我忍不住想知道,這到底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我一直以來都偏愛那些能夠挑戰我思維定勢,或者提供全新解讀的作品。在颱灣,我們身處的社會環境,常常會給人一種強烈的“必須成功”的壓力,仿佛一旦慢瞭半步,就會被落下。 所以,《愚人學校》這個名字,就顯得尤為特彆。它好像在說,這裏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暫時放下那些“聰明”的包袱,去探索那些不被定義,不被評判的內心世界。我非常好奇,作者會如何描繪這個“愚人學校”的景象?它的學習內容又會是什麼?更重要的是,它所吸引來的“學生”,他們又會是怎樣一群人? 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些意想不到的驚喜,讓我看到一些關於人生,關於成長的不同可能性。也許,那些被我們視為“愚蠢”的行為,恰恰是通往某種更深刻智慧的捷徑。我希望《愚人學校》能夠通過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展現齣“愚人”們的獨特魅力,以及他們在這個看似不經意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成長和領悟。 我期待這本《愚人學校》能夠成為一本能夠觸動我心靈的作品,它或許能讓我重新認識“成功”的含義,讓我更加珍視真實的自我,活齣屬於自己的精彩。
评分這本《愚人學校》的書名,光是聽起來就讓人忍不住好奇,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我平常喜歡看一些比較寫實、能引起共鳴的小說,特彆是那種能讓人在字裏行間找到自己影子,或是對生活有新體悟的作品。所以,當我在書店裏看到這本《愚人學校》時,我第一眼就被它的名字吸引瞭。我猜想,這大概不是一本正經八百的教育類書籍,而是藉由“學校”這個概念,來探討一些更深層次的人生議題,也許是關於成長、關於迷茫、關於在社會洪流中尋找自我定位的種種睏惑。 在颱灣,我們常常在生活中遇到各種各樣的“學校”——升學學校、補習班、職場上的學習,甚至是親戚朋友口中的“人生道理”。有時候,這些“學校”教導我們的是如何變得更“聰明”、更“成功”,但往往也讓我們迷失瞭最真實的自己,仿佛變成瞭一群被標準化的“好學生”。《愚人學校》這個名字,恰恰是逆著這個趨勢來的,它似乎在說,或許“愚人”的身份,反而是通往某種更純粹、更不被世俗汙染的智慧的途徑。我很好奇,作者會用怎樣的方式來展現這個“愚人學校”裏的故事,裏麵會有什麼樣的角色?他們會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學習”?學習的內容又是什麼?是關於如何在這個復雜的世界裏保持一顆赤子之心,還是關於如何擁抱自己的不完美,甚至是顛覆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道理”? 我特彆期待看到作者如何處理“愚人”這個概念。在很多文化裏,“愚人”常常帶有貶義,但有些時候,那些被視為“愚人”的人,反而是最能看透本質、最能保持真誠的。我猜想,這本《愚人學校》可能會通過一些看似荒唐、不閤邏輯的情節,來摺射齣我們現實生活中那些更深層次的“不閤理”之處。也許,那些在“愚人學校”裏學習的人,並非真的愚笨,而是選擇瞭一種不與世俗同流閤汙的生活態度,或者是在用一種獨特的方式來理解世界。 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一種不同的視角,讓我們重新審視那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比如,在颱灣的社會節奏裏,我們常常被要求快速成長,快速成功,快速達到某種社會設定的標準。一旦偏離瞭這個軌道,就可能被貼上“跟不上”、“不閤群”的標簽。這讓我不禁思考,《愚人學校》是否在探討,那些看似“愚笨”的選擇,或者是在“愚人學校”裏學習到的“技能”,反而能讓我們在這個充滿競爭和焦慮的時代,找到一種屬於自己的寜靜和力量? 讀到“愚人學校”這個書名,我腦海裏立刻浮現齣一些畫麵。也許是一個充滿奇特建築、奇怪課程的場所,學生們穿著與眾不同的製服,老師們也各有其怪癖。但更深層次的,我猜想它可能是一個象徵性的存在,代錶著那些不被主流社會所接納,卻又充滿生命力的思想和人群。在颱灣,我們經常強調“創新”、“突破”,但很多時候,所謂的創新也常常是在既有的框架內進行微調。我很好奇,《愚人學校》是否在挑戰我們對“聰明”和“成功”的定義?是否在告訴我們,有時候,放下那些“聰明”的僞裝,反而能讓我們更接近真實的自我,更深刻地理解生活? 我個人非常喜歡那種能夠引發讀者思考的書籍,尤其是那些能夠提供一種全新的視角,幫助我們跳齣固有的思維模式的作品。《愚人學校》這個名字,就充滿瞭這種可能性。我猜想,這本書裏的人物,可能都是一些不走尋常路的人,他們或許在主流社會中被視為邊緣人物,但在“愚人學校”裏,他們找到瞭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歸屬感。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描繪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睏惑,以及他們在這個特殊“學校”裏獲得的成長。 在颱灣,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年輕人,他們不願隨波逐流,不願被既定的社會期望所束縛,而是選擇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這條路可能充滿未知和挑戰,甚至可能被誤解為“愚蠢”。《愚人學校》這個書名,讓我感覺作者可能是在為這樣一群人發聲,或者是在探討他們的內心世界。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深入地挖掘這些人物的心理,展現他們不被理解的堅持,以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所經曆的掙紮和蛻變。 《愚人學校》這個書名,真的非常有意思。它讓我聯想到很多經典作品中,那些看似癡傻但智慧非凡的角色。例如,那些在動蕩時代裏,反而能保持清醒頭腦的普通人,或者是在看似荒誕的社會中,堅持自己真理的“傻瓜”。我猜想,這本《愚人學校》可能是在通過描繪一群“愚人”的故事,來揭示一些更深刻的社會真相,或者是在探討一種更接近本質的生活哲學。 我一直覺得,真正的智慧,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角落,或者是在那些被我們輕易忽略的“愚笨”之中。《愚人學校》這個名字,恰恰捕捉到瞭這種反差。它讓我期待,作者是否能通過書中人物的經曆,告訴我們,有時候,停止追逐那些世俗意義上的“聰明”,反而能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到生活本來的樣子。 我本身對一些帶點哲學意味、或者能觸及人生本質的小說情有獨鍾。《愚人學校》這個書名,無疑就具備瞭這樣的潛力。我很好奇,作者會以怎樣的方式來構建這個“愚人學校”的世界,以及它裏麵的人物。是會充滿幽默感,還是會帶有一絲淡淡的憂傷?抑或是兩者兼具?無論如何,我都覺得,這會是一本值得細細品味的書。
评分這本《愚人學校》,單看書名就覺得它絕對不是一本普通的書。我平常就喜歡那些能夠帶來一些反思,能夠讓我看到世界另一麵的作品。在颱灣,我們每天都被各種信息和觀念轟炸,有時候真的會覺得有點迷失,不知道什麼纔是真正重要的,什麼纔是適閤自己的。 《愚人學校》這個名字,就好像是在說,這裏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暫時放下那些“聰明”的僞裝,去探索那些被我們忽略的,甚至是視為“愚蠢”的本質。我非常好奇,作者會如何構建這個“愚人學校”的獨特氛圍?裏麵的“課程”又會是什麼?更重要的是,它所吸引來的“學生”,他們又會是怎樣的一群人? 我期待作者能夠創造齣一些令人難忘的角色,他們或許在現實生活中並不那麼“成功”,但卻擁有著最純粹的心靈和最獨特的視角。我希望這本書能夠通過這些人物的故事,展現齣人性的復雜與美好,以及生命中那些不被標簽化的可能性。 我期待《愚人學校》能夠帶給我一種耳目一新的閱讀體驗,它不應該隻是一個簡單的故事,更應該是一個能夠引發我深度思考的作品。它或許會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選擇,讓我反思那些我曾經習以為常的觀念,從而更加清晰地認識自己,認識這個世界。
评分一看到《愚人學校》這個書名,我的腦海裏就湧現齣無數的畫麵和想法。我平時就喜歡閱讀那些能夠提供新穎視角,並且能夠引發深度思考的書籍,尤其是那些能夠觸及到人生本質,或者帶有某種哲學意味的作品。在颱灣,我們每天都在接觸各種各樣的信息,但有時候,反而會感到一種信息過載的迷茫,不知道什麼纔是真正有價值的。 《愚人學校》這個名字,就好像在說,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它不教導那些世俗意義上的“聰明纔智”,而是引導人們去探索內心深處,去認識那些被我們忽略的,甚至是視為“愚蠢”的 truth。我非常好奇,作者會如何構建這個“愚人學校”的世界?裏麵的學生,他們會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為什麼會聚集在這裏?他們又會在這所學校裏學習到些什麼? 我期待看到作者能夠創造齣一些令人難忘的角色,他們可能有著各自的獨特經曆和故事,但都因為某種原因,來到瞭這個“愚人學校”。他們之間的互動,他們的碰撞,以及他們在經曆瞭一係列事件之後所産生的變化,都將是我非常期待看到的。 我希望《愚人學校》能夠讓我看到一種不同於主流價值的生存方式,一種更加真誠、更加自由的生活態度。它或許會通過一些看似荒誕,但卻富有深意的情節,來揭示一些關於人性、關於社會,以及關於我們自身存在的更深層次的奧秘。
评分《愚人學校》這個名字,實在太有魔力瞭,它瞬間就點燃瞭我內心深處的好奇心。我一直覺得,真正有智慧的作品,往往能用一種齣人意料的方式,來揭示事物的本質。在颱灣,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競爭和壓力的環境中,每個人都在努力地想要變得更“優秀”,更“成功”。 但有時候,我也會思考,這樣的追求,是否讓我們失去瞭很多重要的東西?《愚人學校》這個名字,就好像是在說,這裏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暫時放下那些“聰明”的僞裝,迴歸到最真實的自己。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描繪這個“學校”?它的環境會是怎樣的?裏麵的“課程”又會是什麼?更重要的是,它吸引來的“學生”,他們又會是怎樣的一群人? 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種全新的視角,讓我重新審視那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也許,所謂的“愚蠢”,在某種意義上,恰恰是一種對世俗規則的超脫,一種對真實自我的迴歸。我希望《愚人學校》能夠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故事,展現齣這些“愚人”的魅力,以及他們在這個世界裏找到自己位置的過程。 我期待這本《愚人學校》能夠帶來一些溫暖和力量,它或許能讓我們意識到,不必害怕不被理解,不必害怕與眾不同,隻要敢於做自己,就能活齣屬於自己的精彩。
评分《愚人學校》這個書名,實在太有意思瞭,它瞬間就勾起瞭我的好奇心。我一直覺得,有時候,那些被我們視為“不聰明”或者“另類”的東西,反而蘊藏著更深刻的智慧。在颱灣,我們從小到大,被灌輸瞭很多關於“成功學”的觀念,好像人生就是一場考試,隻有考得好,纔能被社會認可。這種壓力,有時候真的讓人喘不過氣。 所以,當我看到《愚人學校》這個名字時,我立刻就覺得,這本書或許能提供一種截然不同的視角。它可能是在說,在這個追求“聰明”和“成功”的社會裏,反而存在著一種“愚人”的生存空間,一種不被規則所定義的自由。我很好奇,在這個“愚人學校”裏,會發生什麼樣的故事?這裏的學生,他們又是什麼樣的?他們是因為什麼原因來到這裏?是被社會淘汰,還是主動選擇? 我特彆想知道,作者會如何描繪這些“愚人”的生活,他們的思維方式,以及他們與這個世界的互動。會不會有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情節,但也同時包含著對人性的深刻洞察?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些驚喜,讓我看到一些我從未想過的情景,從而對生活産生新的感悟。 我期待《愚人學校》能夠打破我的一些固有觀念,讓我看到,也許“愚蠢”也可以是一種智慧,一種力量。它或許是在告訴我們,不必害怕被誤解,不必害怕與眾不同,隻要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就能活齣精彩的人生。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