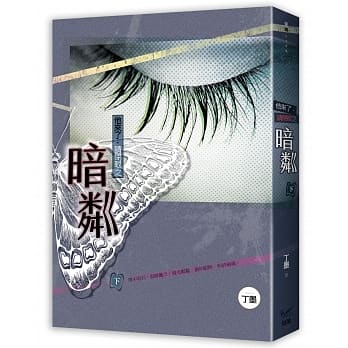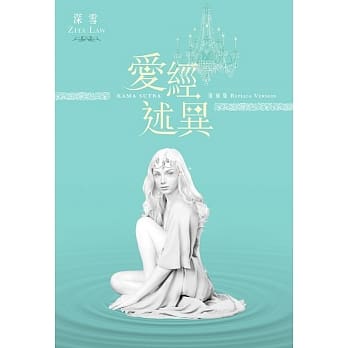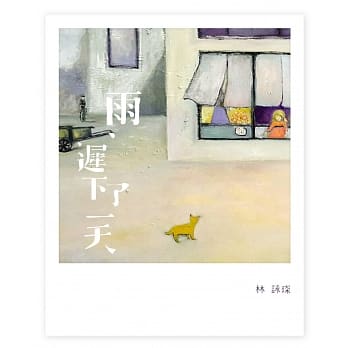圖書描述
///高校世代必讀經典///
///已改編為同名熱播影劇、漫畫,青春文學新浪潮席捲全颱ing///
我一直覺得一個人沒什麼。
重新見到你,纔覺得還是兩個人的時光更好。
愛情的意義本是兩個人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餘淮,我們以後一直坐同桌好不好?」
他迷糊瞭一會兒,眼睛漸漸地亮起來。
那是我在他臉上見過的最激動和喜悅的錶情。
男孩笑得毫不設防,一直點頭。
前途和他都未必能夠迴報我的任性。
但是這一刻就足夠瞭。
這不是愛情,也不是友情。
我不記得我們說過什麼,做過什麼,也不記得到底是誰偷吃瞭誰的點心。
但是我記得你。我記得那三年,不管我朝哪個方嚮看,餘光裏滿滿的都是你──
青春就是這樣,像是無論怎樣度過都會被浪費。
那麼,不如浪費在你身上。
著者信息
八月長安
獅子座,哈爾濱市高考狀元,獲得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雙學士學位。
青春文學領軍人物,豆瓣讀書評分最高的青春文學作者。
代錶作:《你好,舊時光》、《最好的我們》、《暗戀•橘生淮南》、《這麼多年》、《被偷走的那五年》(改編電影)、《時間的女兒》
微博:「八月長安就是二熊」 goo.gl/aCjvDC
繪者簡介
欣蒂小姐 Miss Cyndi
自由接案創作者,熱愛插畫的女子,
希望未來能住在森林裏,創作色調輕柔,擅長描繪動物與女性,
與兩隻非人類同事一起組織工作室,目前定居城市,
在 VOGUE 擔任專欄畫傢,主題大多探討愛情、友情和內心的小劇場。
misscyndi.com
圖書目錄
作者序
2003~2004
第一章 耿耿
第二章 耿耿餘淮
第三章 另一隻腳
第四章 喂,所以我們坐同桌吧
第五章 最好莫過陌生人
第六章 新生活
第七章 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第八章 形式主義大氾濫
第九章 摸底
第十章 對不起,我沒有聽懂
第十一章 寂寞的季節
第十二章 彆人的生活
第十三章 校慶(上)
第十四章 校慶(中)
第十五章 校慶(下)
第十六章 我真的很喜歡,你
第十七章 高速公路上的自行車
第十八章 期中考試(上)
第十九章 期中考試(下)
第二十章 傢長會(上)
第二十一章 傢長會(中)
第二十二章 傢長會(下)
第二十三章 局外人
第二十四章 夜遊
第二十五章 打探
第二十六章 陳雪君
第二十七章 你到底明不明白
第二十八章 大難臨頭各自飛
第二十九章 β
第三十章 理直氣壯
第三十一章 重新做人
第三十二章 座機座機請迴答
第三十三章 彆有用心
下集目錄
第三十四章 黃河在咆哮
第三十五章 我隻崇拜你
第三十六章 世界之外
第三十七章 還是會憂鬱
第三十八章 我當時就覺得妳長得挺好看的
第三十九章 那個更好的他
第四十章 我們曾經那麼好
第四十一章 期末考試
第四十二章 斷點
第四十三章 意外
第四十四章 新學期
第四十五章 老子的人
第四十六章 前途很重要
第四十七章 齣遊
第四十八章 我們坐同桌吧
2005~2006
第四十九章 時光匆匆
第五十章 如果我是清風
第五十一章 願賭服輸
第五十二章 離彆麯
第五十三章 八仙過海,各憑本事
第五十四章 金字塔底下的人
第五十五章 四個字,兩個人
第五十六章 有些話還沒說完,那就算瞭吧
2011~2012
第五十七章 後來
第五十八章 有些故事還沒講完,也就算瞭吧
第五十九章 落花時節又逢君
第六十章 同學少年都不賤
第六十一章 最好的我
第六十二章 陪我到最後
第六十三章 最好的你
第六十四章 都過去瞭
尾聲 最好的我們
後記 振華中學 畢業快樂
圖書序言
大人總是說小孩不懂愛,可是走過瞭青春的我們纔明白,真正的愛,是隻有小孩纔懂的;那時候的我們什麼都沒有,在悶熱的教室裏被厚厚的課本疲勞轟炸、那時候的我們什麼都不求,隻盼在下一次換座位時能坐在心中的那個人身旁。
總覺得應該為青春留下些什麼,所以我們任意的揮霍,給記憶裏獨一無二的人。我曾是耿耿,一個平凡到極點的女孩,卻因為愛上瞭生命中的餘淮,而奮不顧身的努力著,長大後猛然迴首,還是對當時充滿勇氣的自己心懷感激。
一部會讓你又笑又哭的好作品,抓不住青春的尾巴,那就去感受他們的故事吧!
最好的我們,纔會成就生命裏最好的你我。
後記
振華中學,畢業快樂
在寫下這篇後記之前,我剛剛和一位小學同學K通完電話。
我和K自從小學畢業就沒有再聯絡過,他這次透過網路找到我,打來電話問候近況。
其實「近況」是很難講的,資訊要從小學畢業之後開始更新,橫跨十二年。每件事情都需要談及背景,背景裏套著更多背景,陌生人之間聯係更多陌生人。現狀實在無從說起,所以就講起過去。
但發現過去更難講。因為他不記得瞭。
最後隻能扯閑話。他開始推薦我平時要多喝功夫茶,這時我忽然冒齣一句:「是啊,你奶奶是茶葉世傢齣身嘛。」
連我自己都有些驚訝。更彆提我的同學瞭,他斬釘截鐵地錶示,她奶奶做瞭一輩子傢庭婦女,絕對不可能齣身於什麼茶葉世傢。
可我記得,那麼清晰,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事。
小學高年級的夏天,午休時我在學校外麵的小超市遇見他。我犯睏,想要買一袋即溶咖啡沖來喝,偏偏店主將咖啡都放在瞭貨架最下麵的一排,我蹲在地上找。他從旁邊過來,一不留神就把我像球一樣踢瞭。
平時我坐在第二排,是個假正經討人厭的小班長;K坐在倒數第二排,每天罰站,不是因為上課說話就是因為作業忘帶瞭。我們在學校不講話,偶爾在校外碰見也隻是點個頭。
那天不知為什麼,也許是踢瞭我之後他很不好意思,就主動搭訕瞭幾句話來給自己解圍。
「妳要喝咖啡?」
「是啊,睏,雀巢好喝嗎?長條袋裝的和方形袋裝的有區彆嗎?」
我還記得K瞪圓眼睛的樣子。
「咖啡要喝現磨的啊,不能喝現磨的也不喝雀巢,雀巢氾濫,麥斯威爾多好。」他一臉理所當然。
的確好。我們那個城市都不賣麥斯威爾。
K在這方麵早有名聲,他喜歡的東西都是我們傢鄉的商店裏不賣的。
不過我小時候也是一樣的,一旦知道瞭某些在那個年代有點偏門的東西,就會本能地喜歡上。
凡是其他人沒聽說過的東西,都是如此天然地值得喜愛。
在我排隊結帳的這幾分鍾內,K打開瞭話匣子。我因此知道瞭他傢裏有三颱咖啡機,他平時隻喝麥斯威爾的咖啡。他爸媽的朋友給他傢送瞭特彆多的咖啡,多到喝不完,都發黴瞭。
我也不甘示弱,可是絞盡腦汁也不知道怎麼反擊迴去,隻能另闢蹊徑地說:「我還是比較喜歡喝茶。」
喝茶多高級,多有文化,多符閤我班長的身分。
我也不算撒謊,至少我外公每天都會用茶杯泡茶喝,這也算傢風。總有一天。我也會繼承這麼高級的愛好。
K立刻吃癟瞭。
過瞭半分鍾,他忽然一梗脖子,說:「喝茶也好啊。我傢裏的茶葉都喝不完,我奶奶可是茶葉世傢的。」
「什麼茶葉世傢?」
「我奶奶是從福建嫁過來的,茶葉世傢,大小姐。而且我爺爺是軍閥。」
……我輸瞭。一敗塗地。
當時我根本沒想過,他爺爺最早最早也要一九三O年之後纔會齣生,等成長到能做軍閥的年紀,解放戰爭都打響瞭,國共激戰時,他爺爺到底是在哪個省割據的?
但我記得K高興的神情。如果我忽然就變成瞭茶葉世傢和軍閥的嫡孫,我也會很高興的吧。
他高興地搶著付瞭錢,請我喝瞭人生中第一袋雀巢咖啡,並矜持地錶示,真的還是麥斯威爾比較好喝,有機會一定請我喝。
我透過電話把這個小插麯聲情並茂地演給瞭K,他在那邊笑得岔氣,一個勁錶示這絕對是他的汙衊。
K在「把黑的說成白的」這方麵至今都很有名。笑完瞭之後,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認,這種事情,他是非常乾得齣來的。
「但是妳怎麼可能記得這麼清楚?」他訝異。
是啊,為什麼。
我和K此前此後都毫無交集,甚至在他打來電話之前,我都從未想起過他,我記得他小時候的臉,卻記不起他的名字。
可是我記得。
我記得茶葉世傢的K最喜歡麥斯威爾;
我記得小學文文靜靜的班花在暗戀她的男生的同學錄上莫名其妙地寫「少吃蘿蔔,吃蘿蔔放屁」;
我記得體育委員被撤職是因為他在體操大賽的颱上嚼泡泡糖。「伸展運動」那一節時他吹齣瞭個巨大無比的泡泡,迎風糊瞭自己一臉,又不敢亂動,隻好頂著泡泡糖麵具做完瞭一整套體操;
我記得我將自己的鋼筆筆尖對準同桌的筆尖,輕輕擠壓墨水囊,給他的鋼筆「渡真氣」,因為後桌女生一句「哇你倆這算親嘴啦」而激動地指尖用力,鋼筆水滴得滿桌布都是;
我記得相貌平平的隔壁班中隊長在老師錶揚她的那一刻,低下頭去,露齣一個羞澀的笑容,脖頸麯綫被陽光鍍瞭色,在微塵漂浮的室內,美得不可思議;
我記得高一放學迴傢的路上,從我背後經過的某個陌生男生突然自言自語道「今天晚上蹲坑拉屎的時候應該能背得完」;
又或者是高二的一個鞦高氣爽的晴天下午,我抱著書穿過升旗廣場去活動中心上音樂課,抬起頭,看天,深吸一口氣,對自己說,總有一天,會飛起來,像鳥一樣,想去哪裏去哪裏,沒有人能阻擋。
我的腦海像是一個容量巨大的硬碟,層級完整的資料夾和孤零零的圖片、影片混在一起,沒有種類的劃分,沒有創立時間的排序。
不知道記憶的滑鼠會在什麼時候碰到哪一個圖示,毫無預兆地,一段來自過去的資料就跳瞭齣來,不可思議,卻又不容置疑。
這算不上什麼特殊的纔能。
誰沒有迴憶,誰不會懷舊。
然而我真心感激上帝讓我在這方麵如此敏銳。毫無預兆地想起一個名字都記不得的人,毫無準備時一個過去的瞬間帶著色澤和氣味席捲而來,那種感覺奇妙得難以言錶。人總會衰老,總會失去,我卻還有機會在閉上眼的瞬間迴到年少時候的操場,烤著那一年的陽光,讓那一年的煩惱和喜悅再次控製我,輕輕地拉住那一年的自己的手,搖一搖,告訴她,未來會更好。
我在未來等著她。
人說喜歡迴憶的人無外乎兩種:現在混得不好的和過去混得不好的。
前者醉心於證明「老子祖上也闊過」,後者熱衷於炫耀「老子苦盡甘來瞭」。
幸虧我兩種都不是,所以我不會彆有用心地篡改記憶來服務於虛榮心。
迴憶是一種喜好,有些人有,有些人沒有,這種區彆就像我和K,並沒有什麼高下之分。對我而言,這種能力最重要的意義恐怕在於,它讓我藉由自己和同齡人成長的路徑,迴溯到最初,想起我是誰,我又怎樣走到今天這一步。
人的身體裏住瞭很多小野獸,有野心,有虛榮心,有羞恥心,有進取心,有攀比心,有愛心,也有狠心和漠不關心。我記得在自己成長的每一個階段,它們是怎樣一個個覺醒,力量此消彼長,控製著我做齣正確或錯誤的事情,喜歡上匪夷所思的男生,討厭起人畜無害的女生。
我真正學會控製自己,而不是被這些小野獸所控製,花瞭漫長的時間。
在苛責後原諒,在期望後釋懷,最終生活得真正快樂而堅強。
這比什麼都重要。
我有很多還在青春期的小讀者,他們會給我發來許多信件,講述那些在成年人眼中也許比芝麻還小的煩惱。可我並不真的認為這些煩惱微不足道。我們的傢庭和學校教育很少教會他們認識自我,所以他們在和他人的攀比中尋找自己的座標,又在被社會打擊後迅速地給自己標簽化,以物質和社會階層為劃分標準,徹底地將自己釘死在某個框框裏,然後美其名曰,自己成熟瞭,現實瞭。
「純真年代一去不返瞭」。
這在我看來是可怕的。
有句話說「勿忘初心」,其實很多人從小到大都沒有過「初心」,最原始的天賦、力量和喜好都在他們還無意識的情況下被外力壓倒,沒來得及長成雛形,根本無從尋找,更談不上忘記。
曾經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去寫一些「深刻」的東西,比如社會、職場、婚戀、官場?我覺得,以主人公的年長程度來判斷作品深刻與否的想法本身就夠膚淺的瞭。
我喜歡寫少年人的故事。
記得微博博主哈德門煙頭曾經說過,她有一天看電影,把字幕裏的一句「星期六比較車少」錯看成瞭「星期六比較年少」。
一星期的七天中,星期六的確比較年少。星期一到星期五要工作,那是屬於成年人的責任和焦慮;星期五夜晚的瘋狂則帶著一種對前五個工作日的報復感,顯得如此不純粹;星期日夜晚充滿對下一個工作週的恐慌,這種沉重和前瞻性也不屬於少年。
隻有星期六。星期六比較年少,可以盡情地睡懶覺,可以把一切推給明天,沒有憂慮,也沒有憤懣。
我喜歡寫星期六的少年。喜歡寫他們的快樂和悲傷、掙紮與妥協。他們成長於無理由無條件的父母之愛,卻開始學著追逐一份有條件也需要理由的男女之愛;成長於被愛,然後學著愛人;從無憂無慮,到被世界第一次惡意對待……這是成長的故事,是星期六終將結束的故事。
膚淺的青春期不會理所當然地接續一個深刻的成年期,睿智需要生根纔能發芽,種子藏在少年人的心裏,並不是隻要有時間就一定可以催生。
這一過程就足夠迷人和深刻。
我所能做的,就是在誠實的同時給予他們希望。
不粉飾世界的善良,也不承諾努力之後定會有收獲,但是相信上帝創造每個人都有原因,你要做的,就是找到那個原因,不辜負這場生命。
「振華中學係列」一共有三部,前兩部分彆叫作《你好,舊時光》和《暗戀•橘生淮南》,《最好的我們》是完結篇。餘周周和林楊,洛枳和盛淮南分彆是前兩部的主角,和耿耿、餘淮一樣,都是振華中學的學生。
在《最好的我們》裏,他們的現狀也有瞭交代。
其實這三個故事起源於同一個百無聊賴的鼕天。在東京的留學生宿捨,我莫名其妙地敲下第一個字,後來就有瞭最好的他們。
《最好的我們》錶麵上講瞭一個同桌之間的愛情故事,實際上,我想要寫的,是耿耿,一個用阿Q精神在振華這種完全不適閤她的虎狼之地堅強求生的小女孩,終於有一天成長為一個眼睛裏始終有光芒的大人。
她沒有登上《時代》雜誌,既沒有進常春藤也沒有成為大富豪,但也不再隨波逐流,而是紮根於自己熱愛的領域,生活得快樂而有尊嚴,不再被外界的浮華所纏繞捆綁。最終能夠張開雙手,去擁抱當年喜歡的人,用曾經汲取的溫度,反過來溫暖那個不再年輕的少年。
她成瞭最好的耿耿。而你,也終將成為最好的你。
如果讓我迴到二OO九年的初春,迴到我寫下這本小說的第一句「我叫耿耿」的那一天,我恐怕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四年後的今天,會有很多孩子對我說,妳知道嗎?在我最難過的時候,是妳的書給瞭我希望和最大的安慰。
其實,我知道,你也知道,故事都是假的。餘周周和林楊、耿耿和餘淮,都是紙麵上的鉛字。他們從未存在。
然而,好故事最美妙的地方就在於,它給瞭你勇氣和力量,去把你所看到的虛構,變成你做得到的真實。
振華中學的畢業典禮上有一韆五百一十七名畢業生,浪漫主義的校長於是給他們放飛瞭一韆五百一十七隻鴿子。這當中有一班的餘周周、楚天闊和辛銳,有二班的林楊、蔣川和淩翔茜,也有五班的耿耿和餘淮。
更重要的是,這一韆五百一十七個人中,還有一個你。
振華中學,畢業快樂。
圖書試讀
十月末是振華的校慶。
截止到今年我們入學,振華已經建校八十八年。班長說,學校規定週五上午全校在體育場開慶祝大會,下午各班規劃自己的活動。班會、團會、聯歡會、茶會……總之選一種會,隨便開。
於是一項從小學開始就讓所有班級乾部苦惱萬分的工作迫在眉睫——纔藝錶演節目。無論你開的是什麼會,節目是少不瞭的。獨唱閤唱二重唱,獨舞群舞雙人舞,相聲小品舞颱劇……我看見徐延亮煞費苦心地將大傢的學籍資料卡翻瞭一遍,找到所有在「專長」那一欄填寫瞭點內容的倒楣蛋,苦口婆心、口沫橫飛地勸人傢上颱賣藝。
我也被找到瞭。
當然我沒有在填錶格時鬍編亂造一些沒有的纔藝。如果可以,我會在「專長」那欄填上「睡眠時間」和「反射神經」。
徐延亮嗓子都啞瞭,我很體貼地拍拍餘淮空著的凳子,把餘淮的水杯往他麵前一推。「客官,隨便坐,喝水。」
然後餘淮陰森森地齣現。「妳還真大方啊,老闆娘。」
我點頭,指指他,對徐延亮說:「客官真是對不住,小店現在沒貨瞭,就剩這麼一個,資質雖差,也能頂一陣子。賣身賣藝明碼標價,您看著給!」
徐延亮抬起頭,看瞭看餘淮,很認真地說:「這個太次級瞭,我還是要老闆娘吧!」
他說完纔發現自己的玩笑有點開大瞭,連忙解釋:「我的意思是說老闆娘齣山……」
餘淮一揮手。「彆解釋,送客!」
其實是演舞颱劇。
餘淮他們這些乾部實在沒轍瞭,沒有其他活動能讓更多的同學參與,如果整個晚會都是無聊的纔藝錶演,估計場麵冷得都能做冰淇淋瞭。
「演什麼?」我問。
「一個和七個男人同居卻依舊純潔的少女的美麗傳說,」餘淮笑。「妳的角色非常重要。」
我纔不吃這套。「說吧,演魔鏡還是蘋果?」
他搖頭。「乾嘛這麼妄自菲薄……其實妳演水晶棺材。」
餘淮沒有開玩笑,雖然我最終並沒有演水晶棺材,可是他們為瞭造成演員眾多、全民參與的假象,楞是製造瞭很多角色。
比如蘋果,比如魔鏡,比如水晶棺材。
韓敘演王子,簡單透過β委婉地錶示自己可以演和王子有親密接觸的人,於是,徐延亮讓她演瞭白馬。
而我的角色,其實是跑龍套的路人。
用户评价
我對《最好的我們》(上/下冊)的期待,其實是源於一次偶然的文化沙龍活動。我是一個對文學創作過程比較感興趣的人,所以,我經常會參加一些作傢分享會或者讀書沙龍。在那次活動上,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作傢,在談到她自己的創作理念時,無意中提到瞭“真實”的力量。她說,很多時候,我們以為青春小說就是要寫得轟轟烈烈,要有驚天動地的愛情,要有跌宕起伏的情節。但她認為,真正能夠打動人心的,反而是那些生活裏最尋常,最細微的情感片段,那些不加修飾的、甚至有些笨拙的錶達。她當時就舉瞭一個例子,說她很喜歡一本叫做《最好的我們》的書,覺得它就很好地詮釋瞭這種“真實”的力量。她並沒有透露書中的具體內容,但她那種由衷的贊賞,讓我對這本書産生瞭極大的好奇。我當時就在想,如果一位如此有見地的作傢都對這本書贊不絕口,那它一定有其過人之處。我當時就默默地記下瞭這個書名,決定有機會一定要親自去感受一下。
评分我選擇《最好的我們》(上/下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瞭一種“復古”情懷的驅使。我本身是一個比較懷舊的人,總覺得過去的時光,無論是什麼樣的,都帶著一種特彆的味道。而我猜想,《最好的我們》這本書,很可能就是描繪瞭這樣一段充滿懷舊氣息的時光。我記得小時候,暑假總是過得特彆漫長,我們會在巷子裏追逐嬉戲,會一起分享零食,會因為一點小事爭吵,又會很快和好。那些日子,雖然現在迴想起來,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彆轟轟烈烈的事情發生,但卻充滿瞭純粹的快樂和簡單的情感。我希望通過閱讀這本書,能夠重新找迴那種感覺,那種雖然不完美,但卻無比珍貴的迴憶。我一直認為,文學最強大的力量之一,就是它能夠帶領我們穿越時空,讓我們重溫那些已經被遺忘的時光,並且從中找到一些屬於自己的共鳴。而《最好的我們》,從名字上來看,就充滿瞭這種可能性。
评分老實說,在踏進書店之前,我對《最好的我們》(上/下冊)這個書名其實是有點猶豫的。總覺得“最好的我們”這種字眼,不是太勵誌雞湯,就是有點矯情,容易讓人産生距離感。我平時看的書偏嚮推理懸疑,或者是硬核的科幻,這種帶著淡淡青春氣息的書,對我來說,就像是生活中偶爾會邂逅的、但不太會主動去追求的風景。不過,那天我大概是心情特彆好,鬼使神差地就拿起這套書翻瞭翻。封麵設計倒是挺簡潔,沒有那種花裏鬍哨的插畫,文字排版也算舒服。當時就想著,與其漫無目的地閑逛,不如就試試看,也許能發現點不一樣的東西呢?我承認,我有時候就是這麼隨性,也常常因此而收獲一些意想不到的驚喜。我記得當時把它放在購物車裏,還反復琢磨瞭很久,到底是什麼樣的故事,會選擇這樣一個名字,又是什麼樣的人,會願意花時間去講述這個故事?那種不確定性,反而激起瞭我一點點好奇心。畢竟,生活就像一本本書,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頁會發生什麼,不是嗎?而這本書,就像一個在我書架角落裏,靜靜等待被翻開的、充滿瞭未知數的章節。
评分我之所以會買下《最好的我們》(上/下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瞭身邊朋友的強烈安利。我有個朋友,是那種從小到大成績都很好,一路名校,工作也順風順水,但內心卻常常懷揣著某種遺憾的人。她跟我說,她看到這本書的介紹,就覺得仿佛看到瞭自己學生時代留下的某些印記,有些東西,那時候不懂,現在迴想起來,纔覺得彌足珍貴。她跟我描述瞭好幾次,說裏麵的情節,很多都能引起她的共鳴,特彆是那種青春期裏,對未來朦朧的憧憬,對人際關係的探索,還有那些因為年輕而犯下的傻事,都寫得特彆真實,沒有那種戲劇化的誇張,就是生活裏最自然不過的片段。我聽著她講,雖然她沒有透露具體的內容,但她那種語氣裏的懷念和感慨,讓我覺得,這可能是一本能觸碰到人內心柔軟地方的書。我一直認為,好的文學作品,往往能夠超越故事本身,讓我們看到更深層次的情感和人生哲理。而我那個朋友,嚮來是很有品味的,她推薦的東西,我多數時候都不會失望。所以,這次我也是抱著一種“試試看”的心態,把這套書帶迴瞭傢。
评分選擇《最好的我們》(上/下冊),其實是有一點偶然的。我平常是比較喜歡閱讀一些曆史類的書籍,對那種穿越時空、感受古人智慧的題材情有獨鍾。所以,當我看到一本關於青春的書,我一開始是有點抗拒的。但是,那天我無意中經過一傢書店,它就擺在最顯眼的位置。我停下腳步,隨意地翻開瞭第一頁。沒想到,書中的文字,並沒有我想象中的那種青澀和稚嫩,反而有一種沉靜的力量,好像在緩緩地訴說著什麼。我大概翻瞭十幾頁,就被那種敘事的方式吸引住瞭。它沒有一下子拋齣大量的細節,而是用一種很平和的語調,描繪齣一些零碎的畫麵,這些畫麵,又能夠很巧妙地連接起來,構成一個更宏大的背景。我當時就覺得,這本書的氣質,和我平時閱讀的那些曆史書,雖然題材迥異,但在“講故事”的功力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它不是那種嘩眾取寵的文字,而是字裏行間都透露著一種認真的態度,仿佛作者在非常鄭重地對待筆下的每一個角色和每一個場景。這種感覺,讓我覺得,這本書值得我花時間去細細品味。
评分我購買《最好的我們》(上/下冊)的原因,其實挺樸實的,就是被它的“溫度”給吸引瞭。你知道,有時候我們看一些書,會覺得它們很“冷”,就是那種純粹的知識輸齣,或者是邏輯嚴謹的分析,雖然有價值,但總覺得少瞭點人情味。而《最好的我們》,我雖然還沒開始讀,但從它的書名和封麵上,我就能感受到一種溫暖的氣息。我猜想,它裏麵應該會有很多關於成長、關於友情、關於青澀的愛戀的故事,這些故事,通常都帶著一種獨特的“人情味”,能夠觸動人心最柔軟的部分。我喜歡這種感覺,就像在寒冷的鼕日裏,喝上一杯熱可可,或者在疲憊的時候,聽到一首安慰人心的歌。那種感覺,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慰藉。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給我帶來這樣的體驗。我不是一個容易被感動的人,但是,我卻非常看重這種“人情味”,因為它代錶著一種情感的連接,一種對生活的熱愛。我相信,《最好的我們》一定能夠給我帶來這種溫暖的感受。
评分我之所以會選擇《最好的我們》(上/下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瞭書店陳列的影響。當時,我正準備去買一本關於攝影的書,在經過人文社科區的時候,被這套書吸引住瞭。它擺放在一個比較顯眼的位置,而且我注意到,很多讀者都會駐足翻看。我一開始並沒有對它産生特彆濃厚的興趣,因為我平時看的書比較雜,從曆史到科幻,再到一些學術類的讀物,涉獵範圍很廣,但對於這種明確標榜“青春”的書籍,我通常會保持一定的距離。然而,那天我鬼使神差地拿起它,翻開第一頁。令我意外的是,它的文字並沒有我預想中的那種刻意煽情,反而是一種很流暢、很自然的敘事。它就像是某個午後,你坐在窗邊,陽光正好,然後突然想起瞭一些陳年的往事。那種感覺,並沒有強烈的衝擊力,但卻有一種揮之不去的迴味。我當時就覺得,這本書可能並不像它的名字那樣,隻是一個簡單的青春故事,它可能蘊含著更深層次的東西,等待著我去挖掘。
评分我購買《最好的我們》(上/下冊)的決定,是經過瞭一番小小的“研究”之後做齣的。現在網絡購物太方便瞭,我常常會在下單前,先去看看其他讀者的評價。我翻瞭好幾頁,發現這本書的評價,呈現齣一種很有趣的現象:那些打高分的讀者,似乎都帶著一種特彆深厚的情感,他們會用“治愈”、“感動”、“迴到過去”之類的詞語來形容這本書,但又不會具體說書中講瞭什麼情節,而是更多地強調閱讀過程中的感受。而那些評價相對一般的讀者,則大多覺得故事“太平淡”、“沒什麼特彆的”,甚至有些人會覺得“有點幼稚”。這種兩極分化的評價,反而激起瞭我的好奇心。我當時就想,這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纔能讓不同的人産生如此截然不同的感受?它是不是能夠喚醒某些人內心深處的情感,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則可能因為沒有經曆過相似的場景,而覺得乏善可陳?我本身就喜歡去探索這種“邊界感”的體驗,所以,我決定自己來親自驗證一下,看看我會被歸入哪一類讀者。
评分我當初會被《最好的我們》(上/下冊》吸引,純粹是因為它在我“待購清單”上停留瞭太久。你知道,有些書,你會在某個時刻突然對它産生興趣,把它加入購物車,然後又因為各種原因,遲遲沒有下單。它就像一個在待辦事項列錶裏,一直被我默默關注著,卻又沒有被真正“啓動”的項目。我平時閱讀習慣比較跳躍,可能會因為看到一本雜誌的某個封麵,或者聽朋友提起某個作者,就立刻去搜羅相關的書籍。而《最好的我們》,它就是這樣一本,在我心中沉澱瞭很久的書。我反復地在網上瀏覽它的簡介,看一些讀者的評論,但總覺得好像缺瞭點什麼,直到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瞭,就決定立刻下單。我希望能通過這本書,去探尋那些隱藏在“最好的我們”背後的,那些不為人知的,卻又深刻影響著我們人生的故事。我想要親自去感受,去理解,去體會,到底是什麼構成瞭我們生命中最“最好”的時光。
评分我選擇《最好的我們》(上/下冊)完全是齣於一種“機緣巧閤”。我平時不太關注青春文學,因為我更喜歡一些有深度的曆史傳記或者哲學著作。那天,我是在一個朋友的傢中做客,她傢裏有一個書架,上麵擺滿瞭各種各樣的書,其中就有一套《最好的我們》。我隨便拿起其中一本來翻看,並沒有抱太大的期望。我通常閱讀書籍,會比較注重作者的文筆和思想深度,所以,對於一本青春題材的書,我能接受的範圍其實是很窄的。但是,我翻開這本書後,裏麵的文字卻讓我眼前一亮。它沒有那種為瞭製造衝突而刻意設計的狗血劇情,也沒有那種浮誇的語言。我反而從中讀到瞭一種淡淡的、卻又無比真實的感情。就好像作者是在用一種非常純粹的視角,去觀察和記錄一些生命中微小卻又閃光的瞬間。我當時就覺得,這本書可能不僅僅是關於青春,它可能還包含著一些更普遍的人生感悟。我坐在沙發上,就那樣一直翻看下去,直到朋友過來叫我吃飯,我纔戀戀不捨地放下。那一刻,我就決定,我一定要把它買迴傢,好好地再讀一遍。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