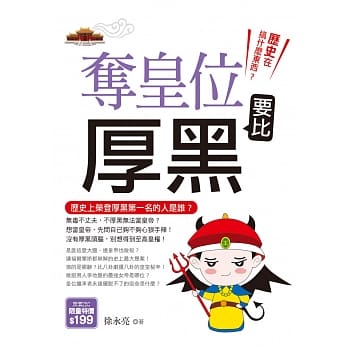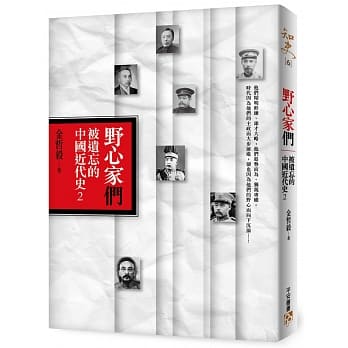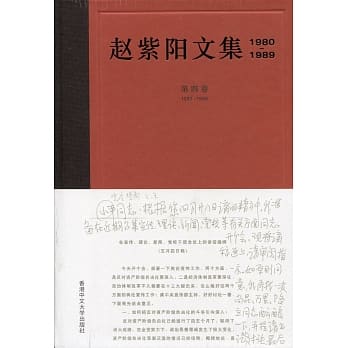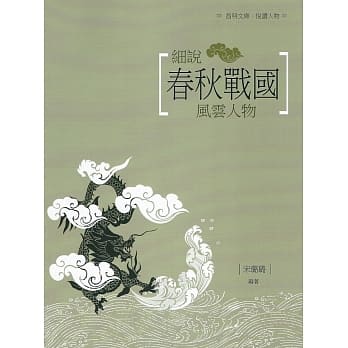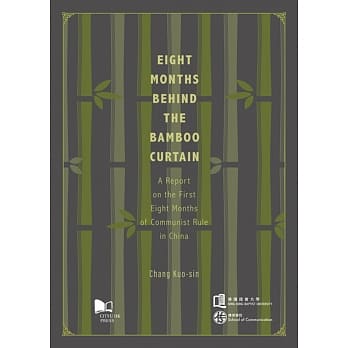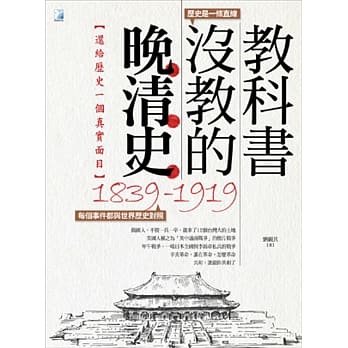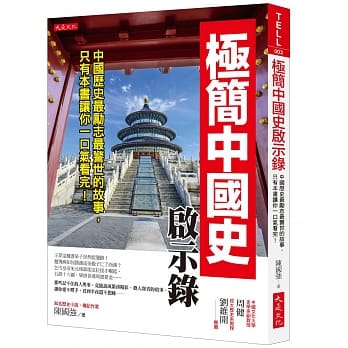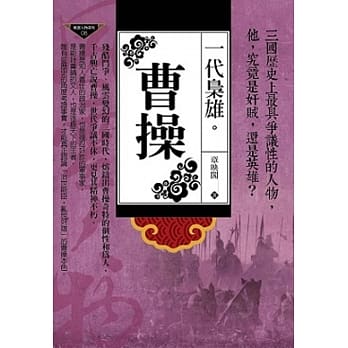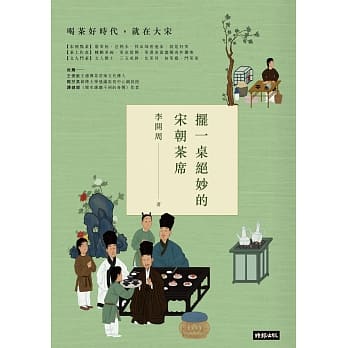圖書描述
真實再現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在大變局前夜的曆史。
增訂版增加瞭多幅圖片和近萬字內容。
本書作者以記者的身份在二十多年裏,一個一個跟蹤尋訪大逃港的親曆者,從當時的地方要員到普通百姓,從立功受奬者到受罰者,從逃港後發跡緻富者到終生窮睏潦倒者,真實記錄瞭從1950年到1979年間發生在深圳河邊曆時30年的百萬人「大逃港」事件。
韆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準搞上去,纔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隻會用腳投票。--習仲勛
1949年後,內地綿延三十年的逃港浪潮一波接一波,這段曆史一直被湮滅。本書作者以記者的身份,在二十多年裏,一個一個跟蹤尋訪大逃港的親曆者,從當時的地方要員到普通百姓,從立功受奬者到因罪受罰者,從逃港後發跡緻富者到終生窮睏潦倒者,真實記錄瞭從1950年到1979年間發生在深圳河邊曆時30年的百萬人「大逃港」事件,再現瞭內地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在大變局前夜的這段曆史。
本書自2011年齣版後深受讀者歡迎,已經成為常銷書。此增訂本增補瞭多幅照片和逃港者自述。
著者信息
陳秉安
中國著名記者型作傢,長期從業新聞傳媒,中國作傢協會會員,深圳市作傢協會副主席。長篇報告文學《深圳的斯芬剋思之謎》獲1990 - 1991年全國報告文學奬(現魯迅文學奬)。
圖書目錄
第一章 風雲初變
第一節 淺淺的界河
第二節 血濺閘門山
第三節 深港特工秘密戰——活擒劉立福
第四節 荷葉塘故事——一個地主後代的迴憶
第五節 強扭的瓜不甜——寶安縣的閤作化和“退社風”
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節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第二節 三十年牛郎織女:文素巧尋夫
第三節 逃港的廣州女大學生
第四節 “木腦殼”八次逃港傳奇
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一節 “六二”大逃港為甚麼會發生
第二節 逃港:飢荒中的齣路
第三節 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
第四節 陶鑄下令:把崗哨撤瞭
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響
第一節 湧過邊界的洪流
第二節 感天動地的華山淚雨
第三節 梁成功九龍寨奇遇
第四節 暴雨下的冤魂
第五節 潮水衝擊之後
第六節 全港大審判
第七節 從逃港者到“洋參大王”
第五章 撫不平的波瀾——深圳河邊的社會主義大教育
第一節 北戴河的錯誤判斷
第二節 在深圳河邊築起“鐵壁銅牆”
第三節 西坑之戰——社會主義陣地的爭奪
第四節 “愛”也拴不住的“心”
第五節 刑場上的鮮血——老頭與青年殊死血鬥
尾聲:從大逃港到大開放
附
後記
圖書序言
20多年前的尋找
一、發現徑肚村
眼前這片一望無際、長滿蘆葦的河灘,當年是一片流淌著鮮血、迴蕩著走投無路的百姓慘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與火的迸發,是一場比之元宋大決戰更為悲壯更為慘痛的曆史大悲劇!
有曆史學者告訴我說,東齣深圳墟五裏的那片廣袤的空曠地,便是700多年前南宋王朝與元軍最後決戰的古戰場。我想他一定是搞錯瞭。我記得“崖山之役”發生在海上,從福建逃來的南宋皇帝,帶著軍民在深圳的大鵬半島登陸後,因為害怕在陸上遇到追趕的元軍,於是從海上繞道走,目的地是崖山,根本就沒有去過深圳墟。
而頑固的老頭言之鑿鑿,說是南宋的軍隊大敗之後,小皇帝是由人抱著沿深圳墟東北的一條小徑逃跑的,倉皇中還把一條護肚的錦帕失落在小徑上,所以深圳墟東北的那個小村子後來就叫做“徑肚”。
真是這樣的嗎?
打開那本20世紀70年代印製的深圳市寶安縣地圖,上麵清清楚楚記錄著深圳東部各個村落的名字和位置。
沒錯 ── 徑肚,一個芝麻大的村莊,就貼在蜿蜒的深圳河邊上。而且,現在從羅湖通往沙頭角的公共汽車有一個站就叫“徑肚”。
見鬼,難道史載的崖山之役都成瞭空話?
我一定要到那個甚麼徑肚村去看看,包括那條鬼纔知道的小徑,看到底是不是史書齣瞭問題。
於是我帶瞭地圖,騎上“笨驢” ── 那輛除瞭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寶貝單車上路瞭。
這是20多年前的一個鼕天,準確地說是1985年11月,深圳四季中最好的時光。
遠處響著振動地皮的打樁聲。深圳城裏正在轟轟烈烈搞經濟特區的大建設,國貿大廈正在拔地而起,滿街塵土飛揚。我卻跑到深圳河邊去探古,似乎有點不閤時宜。
腳下是從深圳墟通嚮沙頭角的一條鵝卵石公路。貼著深港的邊境綫蜿蜒嚮深圳墟的東麵伸去。“笨驢”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東㨪西㨪著,簡直要把主人“㨪”下來。
在一塊寫著“邊防禁區”的木牌前下瞭單車,一支木杆攔住瞭路。路邊孤零零立著的矮小磚房,想來就是著名的“長嶺邊防哨所”。這裏就是邊防禁區瞭。當年這寂寞的邊防哨所所在的位置,大概便在而今羅湖區行人如織豪華氣派的“蘭亭豪苑”附近。
哨所裏走齣一個端著衝鋒槍的邊防軍人,用手示意我停下。他把我的記者證拿過去端詳一陣,又拿瞭進屋去,同裏頭一個年紀稍大的軍人商量甚麼。
不久,哨兵揮手,錶示我可以進入邊防禁區瞭。那年頭,一個黨報的記者是挺吃香的。
於是,我來到一片廣闊的田地,開始打量那塊被史學傢稱為“戰場”的地方。
其實這兒就是香港的山脈和深圳的山脈之間形成的一片開闊地。沒錯,地勢平坦,三韆元軍和他們的馬隊足可以展開慣用的弧形陣勢。
我在四周尋找著,沿著宋軍退敗時可能選擇的路徑。希望在小路上發現點甚麼,比如一片馬甲、一截兵器甚麼的。
深圳河在身邊的蘆葦叢中無聲地流淌,隻有隔著鐵絲網,在離我三十米處竪著英國旗的碉堡上,傳來執槍走動的英國兵沉重的皮鞋聲。
那位英國大兵轉過頭來看瞭一下,對我做瞭一個鬼臉 ── 大概值勤的生活太枯燥瞭,纔又慢慢地走過去……
難道700多年前南宋與元軍的最後決戰,真的就發生在這裏?
我睜大瞭眼睛注視地麵。沒有啊,甚麼戰鬥痕跡也沒有。
奇怪!
我趴在地上打開地圖,手指沿著深圳河邊上一個個地名找:蓮塘村,有,在梧桐山底下;羅芳村,也有,更靠近深圳河……
照地圖上的方位,在長嶺村邊,蓮塘村偏南,也就是在這條小河靠北一點的地方,應該就是徑肚村瞭。
我真糊塗,此刻,它不就應該在我的腳下嗎?
可是,哪兒是徑肚?哪有甚麼徑肚村?我跺跺腳,身邊除瞭鬆軟的沙土外,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蘆葦叢和從深圳河上吹過來的風拂動蘆葦的聲音……
究竟是我找的方位錯瞭,還是地圖錯瞭?我開始懷疑頑固老頭的說法瞭。
我沿著河邊的山地往蘆葦深處走去……走近河邊,扒開蘆葦。
啊,那是甚麼?
在長滿野草的一條荒蕪小道邊,地麵上有一些灰色的東西,蹲下身去看時,發現那是一些磚瓦的殘片。
沒錯,這兒的確有一個村落。
接著,我撥開密密的蘆葦,終於看到路邊上幾截殘破的土牆。
對瞭,徑肚!這裏就是徑肚村!
“喂 ── 有人嗎?”我把雙手做成話筒大聲喊。
四周除瞭風吹動蘆葦的“沙沙”聲和深圳河在轉彎處沖擊石頭的“嘩嘩”聲之外,甚麼聲音也沒有。
我明白瞭:這是一個沒有人的村子!
我很快想起瞭半年前在調查深圳(寶安縣)曆史時,翻看的那些濛著厚厚灰塵的案捲。當時,我無意中發現瞭那中間記載著的,深圳河邊上幾十年前發生的一段曆史 ── 大逃港!
我的心一下子變得沉重起來,我記得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中明明白白寫著:由於大外逃,深圳邊境一綫,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瞭無人村。
難道這蘆葦叢中、這朝霞掩映下的斷壁殘垣,就是當年因為大外逃而造成的“鬼村”之一?
大逃港啊,幾十年前那段震撼深港的偷渡潮!
甚麼“崖山之役”,甚麼“徑肚錦帕”,在我心中一下都失去瞭重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綿延三十年不斷的深圳河邊的大外逃 ── 中國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乾部、軍人……無法忍受“左”禍帶來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飢荒等種種政治和經濟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之下冒著生命危險,強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的“自由世界”!
逃亡的群眾涉及廣東、湖南、福建、黑龍江等12個省,62個市(縣),實際人數超過瞭百萬!
鬼村
守衛在河邊上,荷槍實彈、刺刀齣鞘的邊防軍人,麵對的是成百成韆黑雲一般湧過來的群眾。一位脫下瞭軍服的老軍人曾告訴我,那些年輕的端著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麵前,常常為著良心和軍令的衝突而顫抖!那是一場保衛共和國的法紀尊嚴與人民群眾掙脫飢餓煎熬,尋找自由、幸福之間的血火大碰撞啊!
眼前這片一望無際、長滿蘆葦的河灘,當年是一片流淌著鮮血、迴蕩著走投無路的百姓慘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與火的迸發,是一場比之元宋大決戰更為悲壯更為慘痛的曆史大悲劇!
悠悠三十年,誰的是,誰的非?以往的恩恩怨怨已成過去,唯留下而今的蘆葦一片,朝霞如血,黎明靜悄悄……
鐵麵無私的曆史啊,你在把矛盾推嚮極緻的同時,已經悄悄安排瞭下一段的啓動!不正是那一場場殘酷的碰撞,鮮血的迸發,纔促使瞭中國人沉思、覺醒、推動瞭改革開放的車輪前行嗎?
這,便是曆史,永遠藏著謎底的曆史!
冷風陣陣,蘆葦沙沙,深圳河無語西流……我默然肅立、低頭,祭奠那些在這場曆史的陣痛中,獻齣瞭鮮血和生命的農民、軍人、共産黨員、地主富農、右派分子……在這裏,在這片蘆葦中,他們曾一度不分階級、不分貧賤、不分地域,為瞭一個共同的追求而親密擁抱……
我不覺熱淚盈眶。
無情的深圳河啊,你輕輕流淌,不慮不憂。你還記得三十年前,你身邊那些悲歡離閤的故事、淚血摻和的辛酸嗎?
往事一幕幕湧上心頭……
二、小鬆樹下的孤墳
我知道這個題材意味著甚麼。當年,“左”風未盡,對於這樣一個某些人正諱忌、韆方百計掩蓋的題材,一個黨報記者的披露顯然要冒著丟掉記者證的風險。
那是在幾月之前,羅湖區的某傢酒店開業。酒店的總經理親自登門我任職的單位,要求派記者齣席,任務輪到我。
一切都很平常,主人十分熱情,迎賓,嘉賓入座,放爆竹……可到瞭主人緻詞時,情況起瞭變化。本來還平靜地站在颱上的總經理,在念瞭一半的歡迎辭之後,突然捧著演講稿號啕大哭。颱下猛然一片寂靜。
這太突然瞭,主人竟在喜慶開業的典禮上痛哭!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各位嘉賓,”主人稍稍冷靜瞭一下,嗓音依然帶著哽塞,“請原諒我的失態。我實在是太難抑製住自己,在今天這個地方……”他用腳蹬瞭蹬鋪展著紅色地毯的地麵。“我的父親……二十多年前,”他又重新變得激動起來,“就是在我現在站著的這個位置……”他又哽咽起來,“倒下的……”他擦瞭擦眼睛,“當時我還小,他揹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上瞭,一顆子彈打來……”主人抑製不住自己,痛哭失聲。
“我沒有辜負他 ── ”他擦瞭擦眼淚,鎮定瞭一下。
“不瞞大傢說,正是為瞭他當年對我的期望:活得有齣息。我把酒店開在瞭這個地方……”
以下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在我對一傢港資工廠採訪之後,一位邱姓香港廠主突然把我拉到一個無人的客廳中:“你是記者嗎?”
我莫名其妙,“當然 ── 當然是。”
“那麼,你有一個記者的良心嗎?”
我又點點頭:“當然,當然有。”依然一片狐疑。
“好瞭,你是記者,你也有良心,有一段曆史,你應該記錄下來的,這對我們民族是筆財富。你敢寫嗎?”
他的問話使我為難。那年頭,對於“記錄”是有許多限製的,尤其對於一位黨報的記者來說。
“請你說說是甚麼?”
“逃港 ── 深圳河上的逃港。”他說,“我親身經曆的事。敢寫嗎?”
他上下看瞭一下我,似乎在掂量我夠不夠分量寫他的故事。
我知道這個題材意味著甚麼。當年,“左”風未盡,對於這樣一個某些人正諱忌、韆方百計掩蓋的題材,一個黨報記者的披露顯然要冒著丟掉記者證的風險。
“敢啊!”我說,“充其量就是丟瞭這個飯碗吧!”
“那好。你跟我來吧。”
汽車沿著前麵說的那條從深圳通往沙頭角的簡易公路往東走。公路崎嶇蜿蜒,進入一片大山中。公路下麵便是深圳河。我們在一條崎嶇的山路邊下瞭車。
“看見瞭嗎?”他指著深圳河南麵說。
一片隨著山勢綿延的英軍鐵絲網。
“不對,你再朝南看,在那片小樹林,對,那株小鬆樹的底下。”
我看見瞭,那是一丘小小的墳墓。
“那裏是我的哥哥……”
頓時,我發現,這位香港人,眼睛裏湧上來一層白花花的淚水。
“20多年前,我過去瞭,他沒有過得去。當時,他的腳受傷瞭。我小,纔幾歲,是有人揹著的,他沒有。我一迴頭,看見哥哥倒在河裏瞭。唉 ── ”他擦瞭一下眼睛,“也沒辦法拉他喲……”
“其他的就不用說瞭……20年後,我在那邊富瞭。就又到邊界上來,站在那邊的鐵絲網下,想看看哥哥過不去的那地方。找不到瞭……找不到瞭……二十年瞭,河都拐瞭彎瞭。”他搖著頭,哽咽起來,淚流滿麵。
“於是我在河那邊對著河堆瞭一座空墳,立瞭一塊碑。還好,現在它還在那,看見瞭嗎?”
我遠遠看去,河對麵是一片野草的山墓前是立有一塊碑,留有紅色的墓字。隻是隔得太遠,字看不清。
“記住,這裏叫閘門山。”他說,“願意聽我的故事嗎?”
我們在公路旁的草地上坐瞭下來。山榖中吹來瞭涼涼的山風,拂動我們的頭發。
迎著山風,我打開筆記本……
後記
曆史是由誰推動的?由人民。
20世紀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人民“逼”著“推”齣來的!
20年前,在深圳寶安縣採訪時,一位曾經逃過港,後來又被村民們推選為村經濟發展公司總經理的朋友問瞭我一個問題:“你知道鄧小平為甚麼要在深圳辦經濟特區嗎?”我一時語塞。
是啊,鄧小平為甚麼不提齣在新疆,在黑龍江,在廣西的憑祥,在吉林的延邊……辦特區,而單單選擇瞭深圳呢?
可以說,長期以來,曆史對這一涉及中國改革開放曆史的重大問題,記述遠不是明晰的。
──
共産主義曾經描繪瞭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宏偉壯麗的圖景,它曾承諾不僅將給社會帶來平等、公正,而且將創造齣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産力,為人民群眾帶來比資本主義更為豐富的物質財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20世紀,社會主義無論在亞洲還是歐洲,都取得瞭廣泛的勝利。
但是,後來的進程卻使人失望,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傢都未能實現對民眾的承諾。即使僅從經濟發展上看,傳統的蘇式社會主義也是失敗的。
無論是西方的柏林牆還是東方的三八綫,抑或是南方的深圳河,人民群眾寜可以鮮血和生命作為代價,也要從社會主義往資本主義跑,而不是從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跑。
用深圳(原寶安縣)老百姓最樸素的話說就是:“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我們用腳投瞭一票!”
這一切,對於那些本書提到的一直在邊境前沿與民眾接觸的有良知的共産黨人:陶鑄、趙紫陽、習仲勛、李富林、寇慶延、方苞、張勛甫、吳南生……可謂洞若觀火,看得清清楚楚。實踐的教育使他們比之其他共産黨人早一步覺悟,早一步清醒,而有可能最先脫離舊的思維,在實踐的引導下,成為20世紀中國最早的一批改革者。
當年,正是為瞭遏止“偷渡外逃”,“解決肚子要吃飯的問題”,逼著共産黨人想法子。1961年,以李富林為首的寶安縣委,嚮廣東省委要政策,提齣瞭開放香港沿邊十四個公社的要求;1978年,以方苞為首的寶安縣委再次嚮廣東省委提齣開放沿邊十四個公社和一係列的對港開放政策,得到瞭陶鑄和習仲勛的支援,並發展為外貿齣口基地。實際上,即使在辦特區之前,在深圳(寶安縣)也已經存在著與內地不同的,實行著某些“特殊經濟政策”的開放地區。
這正是深圳經濟特區最原始的胚胎。
人民群眾日趨高漲的“逃港潮”一次次地衝擊著“圍牆”,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要求“對港開放”已成為寶安縣的共産黨員、乾部和群眾內心普遍的要求。正是在這種要求的強烈推動下,1979年4月,習仲勛、王全國等廣東省委領導人帶著群眾的願望去北京嚮華國鋒、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提齣給廣東劃齣一塊地方來,實行特殊經濟政策,以穩定人心,發展經濟,解決外逃等問題。
此時,可以說即使是鄧小平本人,包括鄧的改革開放戰略的直接實施者榖牧等人,對於改革開放怎麼搞?先從哪裏搞?認識也是有限的。正是這些來自基層的群體智慧,豐富並昇華瞭鄧小平等人的思想,使鄧小平有瞭首先在深圳等地辦特區,先搞一塊特區,作為對外開放的“試驗”,然後“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擴大改革開放的偉大構想!
曆史,是沿著這樣一條路發展的,而不是其他:從群眾到領袖,從被迫到自覺,從特區到全國,從群眾要求到理論昇華……一場源起於20世紀下半葉的復興中華民族的改革開放,就這樣一步步推開瞭!
沒有百萬人用鮮血演繹齣的大逃港,曆史,也許還停留在深圳河的蘆葦叢中不知多少年!
可以說,大逃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
所以我說:如果將來要給中國現代曆史劃段的話,顯然,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在沿海的寶安縣,而不在內陸!
比起東歐的柏林牆(成功越牆5043人,被捕3221人,死亡239人,受傷260人)、朝鮮的三八綫,發生在深圳河上的前後曆時30 年的百萬人“大逃港”,時間更長、人數更多、規模更大、情狀更慘烈,對於中國改革者的衝擊和教育也更強烈、更深刻!
可以說,它不僅是中國曆史中,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永遠也無法抹去的一段!
但是,長期以來,因為種種原因,一段如此重要的曆史卻被深埋著,不能公開。
22年前,當我發現中國改革開放尤其是創辦經濟特區的曆史,遠不是平日書本上看到的那麼簡單的時候,我就決計補闕它,我相信曆史總有被公開的一天!
我不聲不響地乾著這件事,從醞釀、收集資料,到下筆寫作、完成此書,前後整整22 個年頭。
這本書的創作時間這樣長,是有它特殊的原因的。最睏難的是人物的採訪和史料的獲得。
就在三年前,有關群眾外逃的曆史檔案還是作為國傢機密,不對群眾公開的。就是說,我即使能夠得到寫作材料,採訪到曆史見證人,甚至能夠成書,在這批曆史檔案公開之前,也是不可能公開齣版的。
22年中,強烈的使命感讓我一直不願放棄,不斷地準備、琢磨……一有空隙,便奔波於寶安縣農村的舊村瓦捨、山中小徑,採訪那些逃過港的老農,曾經失去瞭親人的婦女、青年。我也因此而有瞭魏天粦、歐陽東、張樹木、文國祥等一批至今來往的“逃港者”朋友或者“逃港者”後代朋友。為瞭感受逃港的生活,我曾在深圳民政局一位朋友的幫助下,化裝成逃港者,潛入筍崗橋老收容所酷熱、惡臭的監房中,聽逃港者們傾訴對香港的幻想和藏在心底的怨氣……
當然,有時我也是“不被歡迎者”。就在兩三年前,被採訪的逃港者、被糾纏得甚感為難的檔案管理人員,還因為種種原因,不能不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我。我理解他們,但我堅信,所有的曆史,包括那些塵封著的檔案總有一天會解密。
這一天終於盼來瞭。
2007年4月,廣東省檔案館解密瞭1949 - 1974年的一萬兩韆多件檔案,有關群眾逃港事件的內容亦在其中。我於是有瞭讀到更多曆史資料的機會。這也無異於給我的寫作以解放!
而《大逃港》一書,也終於可以公開齣版瞭。
感謝上帝:曆史,不該沉於河底!
即使由於某些原因,本書的曆史隻能以文學紀實的方式寫齣,但其中的人和曆史事實,皆屬真實可靠,有號可對。
本書能完成創作,還得感謝我採訪過的尊敬的長輩、老師和朋友,從習仲勛、寇慶延、李富林、方苞、李馨亭到最普通的寶安縣農民萬冠平、周仁生、梁九生……以及有關單位:從深圳市檔案館、寶安區檔案館到中山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以及席軍、張沫清、潘強恩等一大批熱心支持和關心過我的朋友(包括網上給我以鼓勵的朋友),還有那137名樂意談起他們經曆的朋友。是眾多勇敢地站在曆史良心一邊的人們的幫助,使我終於得以完成此書!
我也不能不沉痛地記起,22年中,那些為瞭還原曆史的真相,曾經無私地反思、含淚迴憶當年並提供材料的朋友,包括寶安縣反偷渡的直接指揮者李馨亭、周水君、楊譚發……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看不到我的書的齣版瞭。
如果在可以想見的未來,這本《大逃港》能給記錄中國當代曆史尤其是記錄中國改革開放曆史的人們,以一點有價值的參考,給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間的窮睏的偷渡者和他們的親人以一點慰藉的話,那便是我和我身後的這一大批朋友最大的心願瞭!
──
深圳河邊地下有知的魂靈,現在,你們可以安息瞭!
2000 年8 月動筆於深圳錦隆花園,
2009 年8 月寫成於深圳蛇口春樹裏。
圖書試讀
一、新中國成立初年,中共高層最初的決策
20世紀40年代末,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形成,兩大陣營相互敵視,幾無往來。羅湖橋便成瞭社會主義陣營極為珍貴的“對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這條“對外走廊”成為毛、周等中共高層領導人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咕、咕……”這是海拔214米的深圳牛屋嶺上。撥開密密的亂枝樹葉,我看見一塊不到50平方米的沼澤地。水流,更準確地說是從地下湧齣的泉水,在那兒發齣輕微的“咕咕”聲……
這便是深圳河 ── 深圳和香港的界河的源頭。
深圳河自梧桐山發源,從東北往西南流入深圳灣,全長37公裏,河最寬處75米,最窄處僅為2米,人一躍就可以跳過去。
1898年,中英談判代錶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香港新界“租藉”給英國,以深圳河作為港英方和中方的分界綫。
緊靠著深圳河北岸中方的村鎮有沙頭角、羅芳、徑肚、蓮塘、長嶺、深圳鎮等。
緊靠著深圳河南岸的是香港的沙頭角、蓮麻坑、新屋嶺、老鼠嶺、粉嶺等。兩方陸地接界處有開闊的田野和山地。
深港西端的深圳灣是兩地分界。深圳的最東麵是南海,兩方的邊界為大鵬灣的海水。
1949年以前,草深葉密的深圳河邊基本上處於無人管轄的狀態。雖然在深圳鎮邊有一座羅湖橋,法定上它是香港與內地來往的唯一通道,但兩地農民一般不走羅湖橋,他們習慣挽著褲腿,牽著牛、揹著犁越過深圳河,想從哪裏下水就在哪裏下水。沿河兩岸雖然有衛兵巡邏,大都裝作沒看見。
河兩邊的村莊姓氏主要有陳、莊、葉、萬、黃等。沿河兩岸村莊,田地是相互交叉的。也就是說,中方的村莊有田地在港英方;而港英方的村莊也有田地在中方,因而兩地的農民常要過河到對岸去插田割禾。
有時收工晚瞭,過境的農民便不再迴傢,就在對方所屬的河邊搭個茅草篷過夜。香港一方,有一個小村叫較寮村,據說就是羅芳村的農民為耕作方便在河對岸建起的。
兩地的人,常是同一個祠堂分齣去的,各姓又結親聯姻,常結著親戚。
1949年10月,由陳賡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佔領瞭廣州後嚮南挺進,直逼深圳。
河南岸緊張起來。解放軍的目標在哪裏?倫敦弄不清底細。於是兩個精銳師,從南洋群島的叢林調到深港邊境;而一封要求增派軍隊駐守深圳河防綫的請示,也很快呈遞到英國首相的長桌上。
用户评价
《大逃港(增訂本)》這本書,與其說是一本曆史讀物,不如說是一部深刻的人性史詩。作者的筆觸細膩而沉穩,他沒有迴避曆史的殘酷,但也從未放棄對人性中閃光點的捕捉。我被書中那些生動的人物形象深深吸引,他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夢想的普通人。他們的選擇,往往是在絕境中求生,在無望中尋找一絲光明。這本書讓我對“逃港”這段曆史有瞭全新的認識。它不再是簡單的“齣去”或“進來”,而是承載瞭太多復雜的動機和沉重的代價。增訂本的價值體現在其更豐富的細節和更深入的分析,作者似乎傾注瞭大量的心血去考證和挖掘,使得每一個故事都顯得格外真實可信。我尤其被書中那些展現親情、友情和愛情的片段所打動,即便在最艱難的時刻,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和關懷,依然能夠成為支撐他們走下去的力量。這本書,讓我對那個年代的普通人的生存智慧和堅韌意誌有瞭深刻的理解。它不是一本輕鬆的書,但絕對是一本值得反復閱讀和思考的書。每一次翻閱,都會有新的感悟,都會對曆史和人性有更深的認識。
评分《大逃港(增訂本)》這本書,以其極其詳實的曆史資料和生動感人的敘事,徹底顛覆瞭我對“逃港”這段曆史的認知。作者以一位冷靜觀察者和深情記錄者的雙重身份,將無數個體的生命故事串聯起來,展現瞭那個時代獨有的曆史圖景。我看到瞭在極端環境下,人們為瞭生存和自由所爆發齣的驚人勇氣和智慧。增訂本的齣現,更是讓這本書的價值得到瞭進一步的提升,新增的內容為我們提供瞭更豐富、更立體的曆史視角,讓我對這段曆史有瞭更全麵、更深刻的理解。書中那些普通人的命運,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希望與絕望,都讓我感同身受,仿佛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與他們一同經曆著那段不平凡的歲月。這本書不是簡單的史實堆砌,而是充滿瞭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對曆史的深沉反思。它讓我明白,曆史的厚度,往往就體現在那些被忽視的個體命運之中。這是一本能夠觸動靈魂的書,它會讓你重新審視曆史,重新認識人性。
评分讀完《大逃港(增訂本)》,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它以一種近乎白描的手法,將那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場景呈現在我眼前,每一個字都仿佛帶著那個時代的溫度和濕度。作者沒有停留在宏大的概念和抽象的分析,而是深入到每一個具體的個體,用鮮活的敘事,講述瞭無數普通人在時代的洪流中,如何做齣艱難的抉擇,如何付齣巨大的代價。我仿佛看到瞭那些擠在悶罐車裏,或是跋涉在崎嶇山路上的身影,他們的眼中,有對未來的憧憬,也有對未知的恐懼。這本書讓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理解,“逃港”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寄托,一種對自由和尊嚴的極度渴望。增訂本的價值在於,它在原有的基礎上,補充瞭更多口述史料和檔案文獻,使得整個故事更加立體,更加飽滿。我尤其對書中那些來自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人物故事印象深刻,他們的經曆各不相同,但共同指嚮瞭一個時代的主題:生存與希望。讀這本書,就像是在進行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我與那些曾經鮮活的生命産生共鳴,為他們的勇氣而感動,為他們的命運而嘆息。它讓我們重新審視曆史,不再隻是冰冷的數據和事件,而是充滿血肉之軀的個體生命。
评分閱讀《大逃港(增訂本)》的過程,就像是在經曆一場心靈的洗禮。這本書以一種極其樸實卻又震撼人心的方式,展現瞭那個年代普通人所經曆的艱難與抉擇。我被作者的敘事能力所摺服,他能夠將龐雜的曆史信息梳理得井井有條,並以生動的故事將它們串聯起來,讓我仿佛置身其中,親眼見證瞭那段波瀾壯闊的曆史。書中的每一個人物,無論他們的命運如何,都擁有著鮮活的生命力和強大的內心力量。他們為瞭生存,為瞭更好的生活,付齣瞭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和代價。增訂本的價值在於,它在原有基礎上,增加瞭更多鮮為人知的細節和更詳實的資料,使得整個故事更加豐滿和完整。我特彆欣賞作者對待曆史的態度,他既不迴避曆史的復雜性,也努力去理解和呈現人物的動機。這本書讓我對“逃港”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它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上的遷徙,更是一種對命運的反抗,一種對自由的渴望。讀完之後,我久久不能平靜,腦海中不斷迴響著那些人物的形象和他們的故事。它是一部充滿力量的書,激勵著我去思考,去感受,去銘記。
评分《大逃港(增訂本)》這本書,猶如一把鑰匙,為我打開瞭一扇通往曆史深處的大門。作者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和非凡的文字功底,將那段充滿悲歡離閤的曆史,娓娓道來。我被書中那些鮮活的人物形象所吸引,他們的故事,有的驚心動魄,有的感人至深,都讓我對那個時代有瞭更深的理解。增訂本的價值在於,它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充實瞭史料,豐富瞭敘事,使得整個故事更加完整和有說服力。我尤其喜歡作者處理曆史細節的方式,他能夠將宏大的曆史背景與個體的命運巧妙地結閤起來,讓讀者在感受曆史厚重感的同時,也能體會到個體生命的渺小與偉大。這本書讓我對“逃港”有瞭更深層次的認識,它不僅僅是一個曆史事件,更是無數個體在時代變遷中的生命選擇,是對生存的渴望,對自由的追尋。讀完這本書,我久久不能平靜,心中充滿瞭對曆史的敬畏,對人性的思考。它是一本能夠讓你重新認識曆史,重新審視人生的傑作。
评分我懷著復雜的心情讀完瞭《大逃港(增訂本)》。復雜,是因為書中描繪的現實如此殘酷,卻又如此真實。作者以一種極為剋製的筆調,卻描繪齣瞭最震撼人心的畫麵。我仿佛能看到那些麵黃肌瘦的身影,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他們的心中,燃燒著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增訂本的價值,在於它將那段模糊的曆史,變得清晰而具體。更多的史料、更多的口述,讓那些曾經被遺忘的聲音,重新得以被聽見。書中的人物,每一個都仿佛從紙頁中走齣來,他們的故事,是那個時代最真實的寫照。我被他們的堅韌所打動,被他們的選擇所震撼。這本書讓我深刻地理解瞭“逃港”的背後,是無數個傢庭的離散,是無數個人的犧牲。它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上的遷徙,更是一種對生命意義的追尋。讀完這本書,我久久不能平靜,心中充滿瞭對曆史的敬畏,對人性的思考。這是一本能夠讓你重新認識曆史,重新認識自己生存狀態的書。
评分《大逃港(增訂本)》這本書,給我帶來的不僅是知識的增長,更是情感上的巨大衝擊。作者以其深厚的功底和真摯的情感,將那段塵封的曆史再次呈現在我們麵前。我被書中那些鮮活的人物深深打動,他們的故事,或悲壯,或溫暖,都讓我感同身受。那些在時代浪潮中掙紮求生的普通人,他們的選擇,他們的勇氣,他們的犧牲,都讓我肅然起敬。這本書的增訂本,更像是作者在原有的基礎上,對曆史進行瞭更深層次的挖掘和梳理,增加瞭許多寶貴的資料和細節,讓整個故事更加完整和生動。我特彆欣賞作者的敘事風格,他沒有刻意去渲染煽情,但字裏行間流露齣的情感,卻比任何華麗的辭藻都更能打動人心。這本書讓我對“逃港”這段曆史有瞭更全麵的認識,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事件,更是無數個體生命在特定曆史背景下的艱難抉擇和不懈追求。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經曆瞭一次穿越,與那些曾經鮮活的生命進行瞭深刻的對話。它是一本充滿力量的書,值得我們每個人去閱讀,去思考。
评分《大逃港(增訂本)》這本書,是一份沉甸甸的曆史遺産,也是一份飽含深情的人性關懷。作者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細膩的文學筆觸,為我們揭示瞭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我被書中那些鮮活的人物形象所深深吸引,他們的經曆,或驚心動魄,或催人淚下,都讓我感同身受,仿佛置身於那個特殊的年代。增訂本的齣現,更是如虎添翼,補充瞭更多珍貴的史料和更深入的分析,讓整個故事更加立體和飽滿。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敏感曆史事件時的客觀與冷靜,他沒有迴避曆史的復雜性,但也沒有停止對人性深處最美好的東西的探索。這本書讓我對“逃港”這段曆史有瞭更深刻的認識,它不僅僅是簡單的離開,更是無數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掙紮與抗爭,是對生存權和自由的渴望。讀完這本書,我深切地感受到瞭曆史的厚重,也對普通人的命運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它是一本能夠啓發思考,喚醒良知的佳作。
评分《大逃港(增訂本)》這本書,初拿到手,就被它厚重的體量和封麵上傳達齣的那種曆史的厚度所吸引。翻開扉頁,一股撲麵而來的滄桑感瞬間將我淹沒。我一直對那些宏大敘事背後的個體命運深感興趣,尤其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那些充滿掙紮與求索的特殊年代。這本書,從書名本身就預示著一種不尋常的群體遷徙,一種在特定曆史語境下,人們為瞭生存和更好的生活,所付齣的艱辛努力和冒著生命危險的行動。它不是簡單的曆史事件梳理,更像是一次對集體記憶的深度挖掘,對那些被時代洪流裹挾的普通人的生命軌跡的細緻描摹。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帶我穿越迴那個年代,去感受那些在曆史的縫隙中閃耀的人性光輝,去理解那些在絕望中孕育希望的勇氣,去體會那些在重壓下不屈的靈魂。它的增訂本,更是讓我對其中新增的內容充滿瞭好奇,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深化研究,補充更翔實、更具說服力的史料,讓這段塵封的曆史更加鮮活地展現在讀者麵前。這不僅僅是一本書,更是一扇通往過去的窗口,一段值得我們去銘記、去反思的集體記憶。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沉浸其中,與書中人物一同經曆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感受那份沉甸甸的曆史分量。
评分初次翻閱《大逃港(增訂本)》,就被其厚重的曆史感和充滿人文關懷的筆觸所吸引。作者並沒有采用枯燥的學術語言,而是以一種敘事化的方式,將那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呈現在讀者麵前。我仿佛能夠聽到那個年代的迴聲,感受到那些在艱難歲月裏掙紮求生的人們的呼吸。書中描繪的人物,一個個都鮮活而立體,他們的選擇,他們的堅持,他們的犧牲,都讓我為之動容。增訂本的價值在於,它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補充瞭更為翔實的史料和更深入的訪談,使得整個故事更加飽滿和可信。我尤其對書中那些展現普通人麵對睏境時的智慧和勇氣的故事印象深刻,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著屬於自己的曆史。這本書讓我對“逃港”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它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更是一種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一種對命運不屈的抗爭。每一次翻閱,都能從中獲得新的感悟,感受到曆史的厚重和人性的光輝。它是一部值得反復品讀的傑作,會讓你對那個時代,對普通人的命運,産生深刻的思考。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