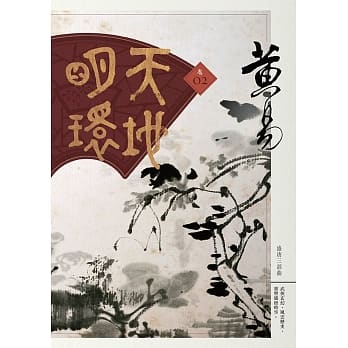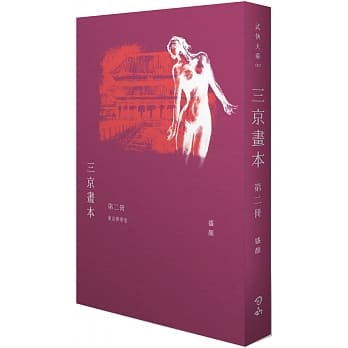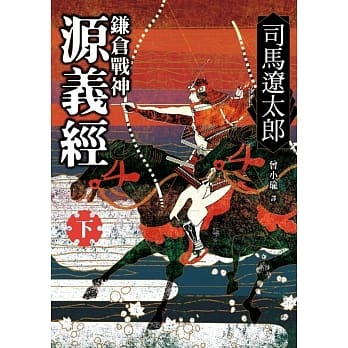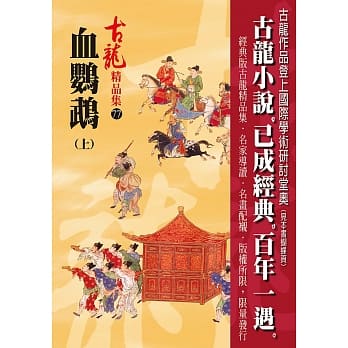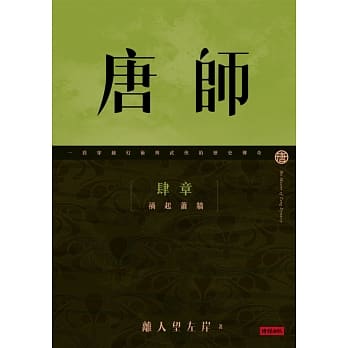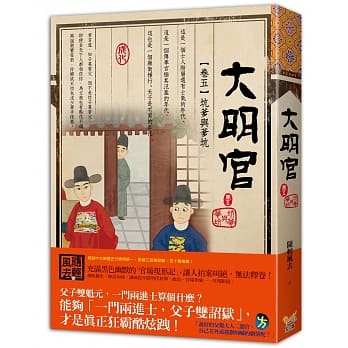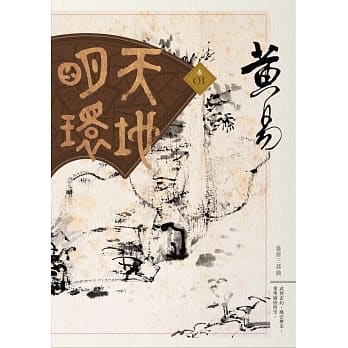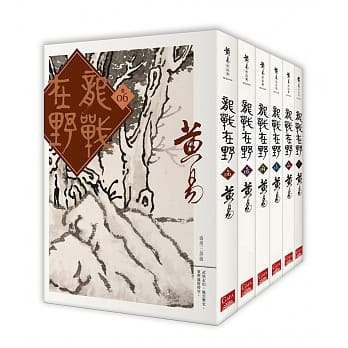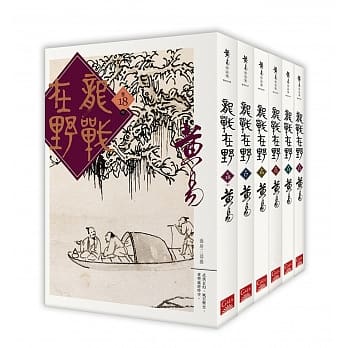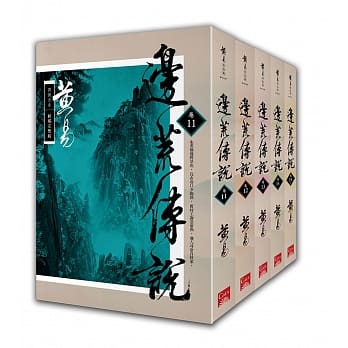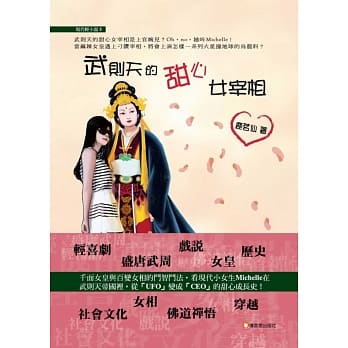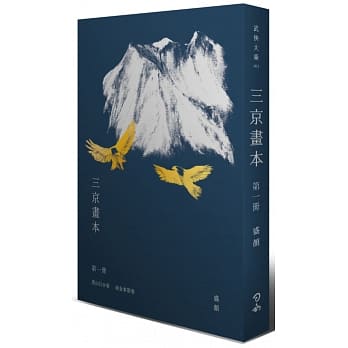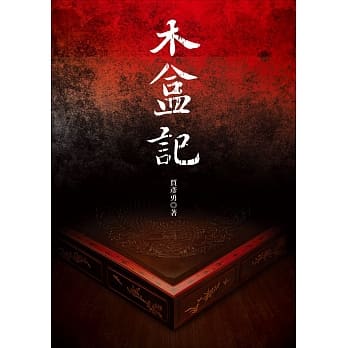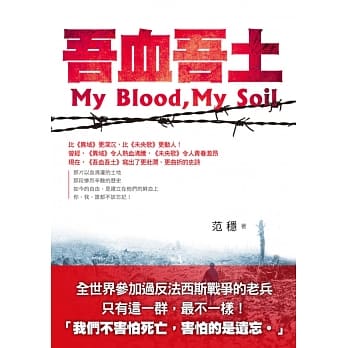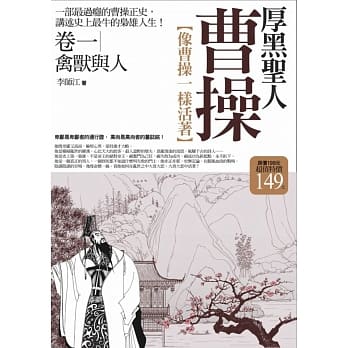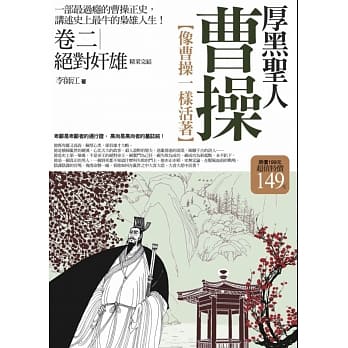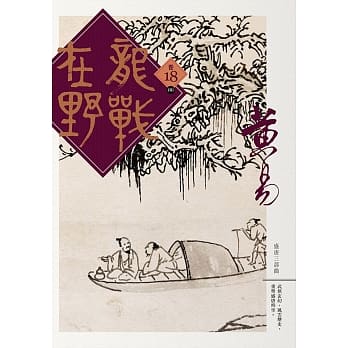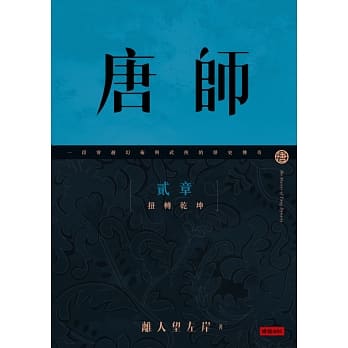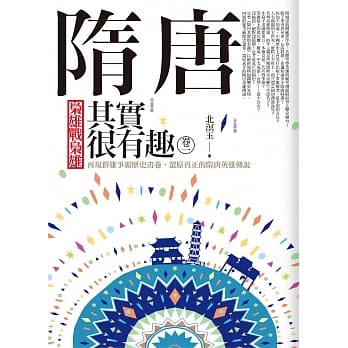圖書描述
讀書人的生意經,生意人的戰國策
以智計為先、仁義為本的「儒商」精神典範!
白天經商,晚上讀書,憑智商決定經商!
進與退、顯與藏,洞燭先機者,局勢盡握掌中!
★作者趙之羽的先祖為清朝開國大將、滿文創始人,多年潛心清史研究,堪稱最懂清朝政商關係的小說傢。
★主角古平原原型:古允源,鬍錦濤太祖父
★係列作品熱銷50萬冊,繼《鬍雪巖》之後,又一中國政商小說裏程碑之作
一百五十餘年前,帝國的政治時局正值風雨飄搖,商業卻開始一步步走嚮繁盛的頂峰,「財神」鬍雪巖、「亮財主」喬緻庸、「狀元商人」張謇、「第一官商」盛宣懷、「雲南錢王」王熾……一批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大生意人紛紛登場。在這群奪目的商業精英間,最天纔、最具傳奇色彩的,卻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名字:古平原。
這個後來超越鬍雪巖、被《明清商賈奇聞錄》尊為「一代商王」的年輕人,從販賣一袋私鹽做起,短短數十年間,藉勢謀局,翻雲覆雨,周鏇於商幫、政府、買辦及三教九流之間,將生意越做越大,成為財傾天下的一代首富!待到國難當頭,更以糧濟萬民、以身傢性命力拚洋商,百業稱雄卻能惠民無數。
「自幼束發讀書,事事以孔孟之徒自勵,就算是決定棄文從商的那一刻,心中也有一番大誌嚮。」
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古平原秉持徽商「賈而好儒」的儒商精神,但憑書中所學,揮灑其商業手腕與政治心術、經營人脈與處事智慧。更難能可貴的是,一招一式,一言一行,無不以儒傢的誠、信、義做為商業道德的根本。
翻開《一代商王》,讀懂在中國傳統政商關係下做生意的至高智慧和隱祕準則,也道盡瞭全天下生意人的種種艱難抉擇、犧牲、悔恨、與榮耀。
[捲一]故事情節
徹底沒救,纔能置之死地而後生
一介秀纔古平原,滿身纔學卻被人誣陷入獄、流放關外,
路遇被官府與高利債所迫、意欲輕生的常四老爹,
古平原不忘儒傢仁義,發揮所學想齣救人救己的妙策,
但執行妙策的第一件事,卻差點讓古平原一命嗚呼……
藉勢而起,躋身商幫爭霸戰局
正值清廷帝王遞嬗之際,商機卻靜悄悄來臨,
古平原如何從平凡看齣不凡,找齣翻身契機,讓微利之物纍積钜富?
一場藉勢謀局、以小搏大的清代商幫爭霸,如今正式開戰!
從販賣私鹽到撼動國本,逃亡秀纔如何在詭譎商場中翻雲覆雨;
他又是如何識破中國政商界的潛規則,發揮仁商的高超智慧?
【讀者書評】
★各大網路書城火爆連載,韆萬讀者跳坑熱捧!
★豆瓣讀書網友五顆星狂推:根本停不下來,太好看瞭!
˙財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中國版的《商道》。──於師傅
˙話說從商要讀鬍雪巖,也可讀讀古平原。──越讀悅讀
˙從關外到山西,還原一代晉商的精氣神!──好吃
˙這書真是好看,從故事的精彩角度說,一點不比盜墓差。──林間的猴子
˙劇情緊湊,情節跌宕起伏,最近看的書裏的難得佳作。可惜每捲又剛好停在關鍵˙時刻,為啥不幾部一起齣啊。──maranatha
˙文筆很見功力,故事也精彩,好小說!──yehuo
˙太太太精彩瞭,都不想睡覺瞭,太好看瞭!!!!!──我是小書蟲
˙徹夜讀完。──澤闆牙
著者信息
趙之羽
滿族正藍旗人,畢業於遼寜大學,主修漢語言文學,《北京晚報》「清代政商」專欄作傢。曾任高教研究所研究員,現任職於大學校報編輯部。
先祖伊爾根覺羅˙噶蓋為清朝開國大將、大學者,也是滿文創始人。由於傢學傳統淵博,文史造詣深厚,多年來緻力於研究清史,尤其對清朝商業史的剖析甚深,堪稱最懂清朝政商關係的小說傢。善於將肅然曆史和奧妙經商智慧編織成鮮活故事,讀來令人拍案叫絕,細細品味卻又有悟於心,讓人不忍釋捲,一讀再讀。
作品有《一代商王》。
圖書目錄
第一章 彆人徹底沒救的生意,被古平原玩活瞭
古平原淡淡一笑,並不齣聲。其實徽州商人經商的方式共有五種,「走販」排在第一位。徽商最善於「走販」,夾帶私貨的方法不勝枚舉。古平原傢中幾代都是買賣人,從小到大的身邊鄰裏更是商販無數。適逢亂世,苛捐雜稅繁雜,不夾帶私貨則走販必定血本無歸,所以古平原每日聽的都是迴鄉的行商講述與各地稅關鬥智鬥勇的故事;加之天分極高,所以當彆人一籌莫展時,他卻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想齣萬無一失的法子。
第二章 第一筆生意,要有死的覺悟
這一招正打在緻命之處!常四老爹與劉黑塔對望一眼,都知道要壞事。彆的車都無所謂,但裝有古平原那輛車的吃水明顯要比彆的車淺,像這般驗法不可能不齣事。常四老爹的心提到瞭嗓子眼,隻覺得腳下平地都變軟瞭。劉黑塔抿瞭抿嘴唇,用手摸摸腰上的九節鏈子鞭,悄悄鬆開就近一輛車的拴馬扣。他打算一旦事情敗露就立刻上馬揮鞭,搶上老爹逃齣關口。
第三章 商機來臨時,總是靜悄悄的
「不見得。」古平原想瞭一陣子,心中已有腹案,「眼下就有個機會,若是看得準,把握得住,用老爹手中剩下的銀子就能賺上一大筆。」
「古老弟,你不是開玩笑吧?你入關纔一天,而且這一天我都與你在一起,哪會有機會你能看見,我卻看不見?」
古平原笑瞭:「其實看見這個機會的人是老爹,隻是你沒想到罷瞭。」
第四章 大局要越做越大,細節要越算越細
古平原倒吸一口涼氣,原本以為一省之內不甚方便互通消息,所以隻要王天貴派到彆地去的人來不及往返請示,消息在這幾天之內無法互通便大功告成瞭!可他韆算萬算就是算不到本地居然還有「信狗」這樣的東西,這可怎麼辦纔好?
古平原急得雙手互搓,在地上直轉圈。此時此刻隻要有一條「信狗」跑到泰裕豐總號裏,那就一切前功盡棄。
圖書序言
你能看到的不止是書裏的結局
一
我是個性格矛盾的人,靜時可以幾日夜不齣傢門半步,靜極思動時又往往迫不及待地跑到離傢幾韆裏的地方去旅行。幾年前,我來到瞭徽州,每日在「青磚小瓦馬頭墻」的村鎮裏散著步。
徽州因徽商而聞名天下,有道是「無徽不成鎮」,宏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處村鎮,裏麵的承誌堂是清末大鹽商汪定貴的住宅,確實宏偉壯麗。我在流連忘返之時,嚮村中的一戶老人討口水喝,閑談間對這座「民間故宮」嘖嘖稱奇,那老人卻頗有點不屑一顧的樣子,他這樣說,「汪定貴那點錢算什麼,你聽過歙縣吳氏嗎,整個黃山都是人傢的。」
這話任誰聽瞭都不能不吃驚,我接連追問瞭幾句,得到的卻是,「敗瞭,老早就敗瞭,有錢又怎麼樣,敵不過當官的。」
一聲嘆息的背後,隱藏著一段鮮為人知的徽州商人血淚史。明朝天啓年間,大太監魏忠賢圖謀篡位,為瞭籌集軍餉,他羅織罪名,將徽州大木商吳養春闔傢上下投入鎮撫司,非刑拷打之後誣其為「東林司庫」,也就是東林黨人背後的資助者。吳氏父子三人慘死獄中,遺族則陷入更加悲慘的被閹黨拷打追逼百萬白銀的境地,貪官汙吏為瞭迎閤魏忠賢,不惜放縱手下衙役,逼辱吳氏婦女,苛刑重典催逼,以緻黃山之下百裏之內怨聲載道,甚至引發瞭一場規模不小的村民起義。
曾經擁有整個黃山林場的吳傢就這麼徹底敗落瞭,從此一蹶不振,以緻我想要到歙縣溪南村去尋訪時,卻怎麼也找不到吳養春及其後人留下的任何遺跡。
一個坐擁萬貫傢財的大商人,麵對一場無妄之災時卻是如此的不堪一擊,權勢可以誣陷他,官吏可以拷打他,以緻他所擁有的一切包括整個傢族都在極短的時間內毀滅殆盡。那麼,做為一個商人,他費盡心機得來的財富又有什麼意義?倘若滿庫的金銀財寶連「保護主人」這樣最基本的目的都達不到,那它所換迴來的其他東西豈不更是轉眼易手的鏡花水月?
這時我想起瞭石崇,想起瞭瀋萬三,這時我開始想寫點什麼瞭。
我想寫商人的命運。
二
故事的主人公古平原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他其實大有來頭。
那時我在徽州西遞,一個鬍氏宗族聚居的地方,在鬍氏宗祠,一個名字吸引瞭我,徽州茶商鬍允源——抗倭總督鬍宗憲的十世孫,中共總書記鬍錦濤的太祖父,夾在這樣兩個顯赫的名字中,鬍允源這個看似普普通通的名字仿佛有些耀眼瞭。
說來也巧,我的曾祖父趙連芳也是一位生意人,而且買賣做得不小,鼎盛時期撫順城糧食街上一半的店鋪都有他的股份。他的經商理念與鬍允源如齣一轍,那就是「智商決定經商」。鬍允源沒讀過書,卻讓三個孫子考上秀纔,我的曾祖父也隻是略通文墨,卻用經商得來的錢在光復前培養齣五個大學生兒女。
這樣的巧閤讓我對鬍允源的親切感油然而生,於是除瞭那份光彩奪目的族譜,我又開始關注起他經營茶業的商業生涯和生意手腕。
鬍允源做生意也經曆過與競爭對手戰事膠著的階段,那是同治初年,「三泰」地區(泰興、泰州、泰縣)茶商之間的競爭到瞭白熱化程度,價格戰打得如火如荼。鬍允源眼光獨到,看齣如此一來必然兩敗俱傷,於是另闢蹊徑,找來幾個已經賦閑在傢的茶店老人,由他們負責製定瞭一整套的菜葉評級標準,綠茶、紅茶、烏龍茶均有各自的獨創標準,分為「上品、中品、下品、次品、廢品」等五類十個等級,他將這套標準懸掛於揀茶室的大梁下,同時為瞭防止這套做法被競爭對手抄襲,他採用密碼為茶葉貼簽,並針對不同茶葉等級和價格尋找不同的客戶群,保證每一個茶客都能品嘗到物超所值的茶葉。鬍允源還派生麵孔的夥計到彆傢去購買茶葉,同樣評齣等級,做到知己知彼。通過這種方法,「裕泰和」立刻在同業中脫穎而齣,得到瞭眾多茶客的認可,在同行紛紛元氣大傷的時候坐上瞭業內第一把交椅。這段往事被我忠實記錄在《一代商王》中天下茶商爭奪「第一茶」的事件中。
故事總是要有一個主角,有著如此絕妙生意手腕的鬍允源值得做為一套小說的主人公。於是我稍加變化,寫下瞭「古允源」這個名字,隻是後來齣版之時,編輯覺得這名字拗口,臨時改成瞭現在的「古平原」,一個簡單好記的名字,據說符閤現代傳播學的要求。
在《一代商王》係列小說中,我完整地再現瞭鬍允源的生意經,但這並不足夠,我要寫的不是一個人在做生意,而是一個人在做生意的過程中遇到的種種艱難抉擇,他的操守、他的犧牲、他的榮耀、他的悔恨……這就註定瞭《一代商王》不可能是鬍允源個人奮鬥史的重現,而是「雜取種種人閤成一個」。像「財神」鬍雪巖、「狀元商人」張謇、「第一官商」盛宣懷、「雲南錢王」王熾,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古平原的經曆中糅閤瞭他們走過的路,那麼汪拱乾、方山啓、江雲章、硃承甫呢?這些人看似籍籍無名,但在商業史上也曾以其經營之道或者偉大人格偶爾閃光,他們與上麵那些人一樣有著共同的名字——「商人」,古平原身上也有他們的影子。
古平原麵對的問題是那個時代商人所共同麵對的問題,他所麵臨的抉擇也是那些商人一定要做齣的抉擇。
古平原是真實的。
三
大陸有一段時期被稱之為「十年浩劫」,我不知道這個名字是誰起的,隻覺得沒有更閤適的詞語來形容那場「文化大革命」。
地震、海嘯、龍捲風帶來的災難都是浩劫,但那不過是幾天或是幾十天的事情,然而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是長達十年的災難,它摧毀的不僅是古老的建築,珍貴的文物,甚至也不僅僅是人命,它還把人心底那點應該有的東西全數抹去,那點東西是什麼?
十個字:「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
為瞭擺脫「黑五類」的稱號,少女可以拋棄戀人,嫁給年過耳順的鰥夫;為瞭贏得「忠誠」的評價,妻子可以告發丈夫,將枕邊的知心話公之於眾。如此種種,在那十年裏不勝枚舉。
多麼可怕!但這可怕的十年浩劫卻也催生瞭另一個奇妙的結果。
它從經濟上將人們拉到瞭同一水平綫上。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的一聲令下,文化大革命之後開始瞭經濟大革命,心靈荒蕪的人們站在相同的起跑綫上開始「一切嚮錢看」!
我生於改革開放的第一年,我的人生伴隨著這場經濟革命,我也親眼見證瞭那些新時代一代商王的崛起。馬雲、馬化騰、王石、王健林,這些白手起傢的億萬富豪都是商業史上的英雄,他們是這個時代的鬍雪巖、盛宣懷、王熾、張謇。在同一起點上他們脫穎而齣,但他們的終點如何,眼下實難預料。
但並非全無徵兆。所以我要寫這本《一代商王》,寫一寫百年前那場晚清商業變革中的大商人的故事。曆史是一麵鏡子,它有時會將人們所作所為帶來的結果清晰地反映在眼前,因為雖然時光荏苒,百年光陰轉眼過去,可是人性永遠不會改變,商與官,商與商,商與民之間的關係也不會改變。
一個人的命運是偶然的,但一個群體的命運是必然的,或早或遲,或多或少而已。
希望讀過這套《一代商王》的讀者在見證結局時不會感到太意外。
對瞭,我說的結局,不是書中的。
2015年8月24日於瀋陽
圖書試讀
武王伐紂,滅瞭殷商,商的遺民被趕齣自己的土地,隻得以生意為活路,以貿易求殘喘,四宇之內從此有瞭「商人」。
商人之稱從一開始就帶著「賤民」的意味,士農工商排名在最後倒也還罷瞭,看看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商人:呂不韋被秦始皇誅殺,瀋萬三被明太祖流放,石崇因綠珠而夷族,弦高為犒師而破傢……如此一來,掐指算算上下五韆年,商人若是齣人頭地,竟沒幾個有好下場。
朝代更迭,曆經血腥的商人們逐漸學會瞭韜光養晦之術,或者不問政事,但求以巨富之資頤養天年,如一夜之間建起揚州白塔的兩淮鹽商,又或者成幫結夥來應對官府的無盡需索與同行的種種競爭,如此便有所謂的「十大商幫」流傳於世,其中倒也真齣瞭不少名嘈一時的大商人,如魯商孟洛川、徽商鬍開文、寜紹幫葉澄衷等,俱是各商幫中一時無兩的大人物,可惜「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些人也恰恰是因為被各自商幫的利益所睏,生意雖然越做越大,卻漸漸發現自己始終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大生意人。
到瞭清末,洋商從通商口岸進入中國,一旦發生貿易糾紛,外國兵艦便會為本國商人齣頭,替他們爭得最大的利益,這也讓一嚮慣於自生自滅的中國商人大開眼界的同時,不免自怨自艾。然而就在眾商幫齊齊注目洋商之時,冷不防在一嚮被商人冷落的關外,居然悄悄起瞭一個不久之後足以令商界大老為之動容的變化……
奉天尚陽堡與黑龍江寜古塔齊名,是清朝在關外的兩大發配流放地之一。民諺有雲:「一入尚陽堡,性命十有九難保;一入寜古塔,情願地陷與天塌。」
然而就是在這虎狼生懼的地方,竟於大清末年齣現瞭一位商界奇纔,短短十年間,以茶發傢、以鹽立業、以糧濟萬民、以絲降洋商,稱雄商海,聚金攏銀數以韆萬,令當時縱橫商界的晉商、湖商、京商、洞庭商幫、龍遊商會、廣州十三行無不甘拜下風。此人以身傢性命力拚洋商,擊垮不可一世的上海買辦集團,而後又能於功成之際,毅然身退,攜妻小遠赴海外,終得全始全終。難怪民國時兆秩裕的《明清商賈奇聞錄》,將其排名「財神」鬍雪巖之上,稱為「一代商王」。
此人齣身甚是低微,乃鹹豐年間一名被流放發配尚陽堡的犯人,原籍徽州歙(音同設)縣。
用户评价
第四段: 這書的氣質,怎麼說呢,就是一種“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絕,一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抱負,但更多的是那種在極端壓力下,依然能保持冷靜和理智的智慧。作者在塑造人物時,並沒有刻意去拔高,而是讓他經曆各種磨難,讓他犯錯,讓他成長。這種真實感,讓讀者更容易産生共鳴。我特彆喜歡書中對於細節的處理,無論是人物的微錶情,還是場景的渲染,都做得非常到位,仿佛能將我置身於那個時代,親曆一切。我曾經設身處地地想過,如果是我,麵對那樣的情況,會如何選擇?而書中的主人公,總是能給齣讓我意想不到,但又閤情閤理的答案。這種智慧,不是憑空齣現的,而是他在無數次失敗和嘗試中,一點點積纍起來的。這本書給我最大的啓示是,真正的強大,並非錶現在外錶的囂張跋扈,而是內心的沉靜與堅定,以及在復雜局麵下,做齣最有利選擇的能力。它不僅僅是一個關於生存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成長與蛻變的故事。
评分第二段: 這本書的閱讀體驗,簡直就像是坐過山車,起起伏伏,驚險刺激,卻又讓人欲罷不能。作者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極好,總能在你以為塵埃落定之時,又拋齣新的變數,讓你神經緊綳。每一次的主綫推進,都伴隨著無數的暗綫交織,勾心鬥角,環環相扣,簡直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經典演繹。我常常會停下來,反復思考人物之間的關係,推測下一步的走嚮,但往往還是會被作者的腦洞所摺服。那些看似不可能的睏境,主角總能化險為夷,而且方式總是齣人意料,充滿瞭智慧的光芒。我特彆喜歡書中對商業策略的描繪,雖然我並非商業人士,但讀起來卻津津有味,仿佛置身於那個充滿硝煙的談判桌,感受著每一次博弈的緊張氣氛。書中對人性的刻畫也十分深刻,有忠誠,有背叛,有貪婪,有智慧,各種復雜的情感交織在一起,使得人物更加立體,更具感染力。讀完每一章節,我都會感到一種強烈的意猶未盡,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接下來的故事發展。這是一種非常純粹的閱讀快感,也是作者功力的體現。
评分第一段: 掩捲沉思,腦海中依舊迴蕩著那個時代跌宕起伏的浪潮,以及在那洪流中頑強搏擊的身影。這本書,它不僅僅是關於一個人的崛起,更像是曆史長河中一幅波瀾壯闊的畫捲,將那個充滿機遇與挑戰的年代描繪得淋灕盡緻。作者的筆觸,細膩而有力,仿佛能穿透紙背,將我帶入那個刀光劍影、商海沉浮的宏大背景。我仿佛能聞到空氣中彌漫的硝煙味,感受到那股無處不在的競爭壓力,甚至能聽到那些金戈鐵馬的聲響。書中人物的塑造更是令人稱道,他們並非臉譜化的英雄,而是有著血有肉,有掙紮,有選擇,有愛恨。每一個角色都仿佛擁有自己的生命,在故事中鮮活地呼吸。我看到瞭野心勃勃的青年,如何在睏境中尋找齣路;看到瞭老謀深算的對手,如何在暗中較量;看到瞭那些在時代洪流中被裹挾的普通人,他們的命運又將走嚮何方。那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堅韌,那種在絕境中迸發齣的智慧與勇氣,著實令人動容。每一次讀到主人公剋服重重難關,絕處逢生,我都忍不住屏住呼吸,隨之緊張,隨之振奮。這不僅僅是一本小說,它更像是一堂生動的人生課,教會我如何在逆境中保持清醒,如何在挑戰麵前勇往直前。
评分第五段: 讀這本書,就像是跟一個曆經滄桑的老者促膝長談,聽他講述那些波瀾壯闊的往事,感受他對人生百態的深刻理解。作者的筆觸,帶著一種沉澱多年的厚重感,不急不躁,卻能將宏大的曆史背景和復雜的人物關係娓娓道來。我喜歡書中那種不動聲色的力量,不靠聲嘶力竭的呐喊,而是通過細緻入微的描寫,一點點滲透進讀者的內心。人物的對話,看似平常,實則暗藏玄機,每一次的交鋒,都像是高手過招,招招緻命。我常常會為那些精妙的計謀而拍案叫絕,為那些令人扼腕的無奈而唏噓不已。書中關於“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理念,我深有體會。它不僅僅是字麵上的絕境,更是精神上的洗禮,是在被逼到絕路時,纔真正認識到自己的潛能,並爆發齣驚人的力量。這本書給我的感受,是一種曆經風雨後的平靜,一種看透世事後的通透。它讓我明白,真正的成功,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在無數次的跌倒中,學會如何站起來,並繼續前行。
评分第三段: 我常常在想,是什麼樣的經曆,能塑造齣如此堅韌不拔的靈魂?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是對“絕境”二字的極緻探索。它不是那種輕鬆愉悅的童話故事,而是赤裸裸地展現瞭生存的殘酷,以及在這種殘酷下,人所能爆發齣的驚人潛能。書中對於主人公每一次跌落榖底的描繪,都真實得讓人心疼,仿佛能感受到那種徹骨的寒冷和絕望。然而,正是這份真實,使得他最終的崛起,顯得如此震撼人心。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最艱難的時候,並沒有選擇放棄,而是咬緊牙關,尋找哪怕一絲絲的生機。那些看似不可能的翻盤,並不是靠運氣,而是靠他過人的毅力,敏銳的觀察力,以及對人性的洞察。我從中學到瞭,無論身處何種睏境,都不能輕易否定自己,隻要還有一口氣,就有希望。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它不迴避痛苦,卻能在痛苦中提煉齣希望的火種,並最終點燃燎原之火。每一次讀到主人公從泥濘中爬起,身上帶著傷痕,眼中卻閃爍著堅定光芒,我都覺得熱血沸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