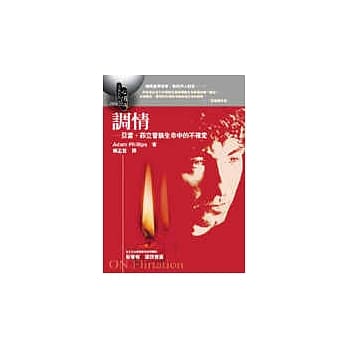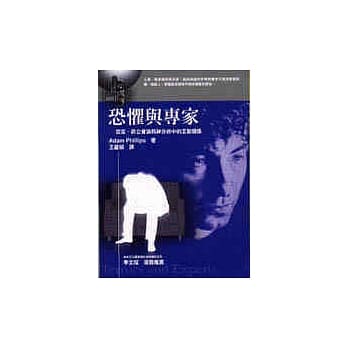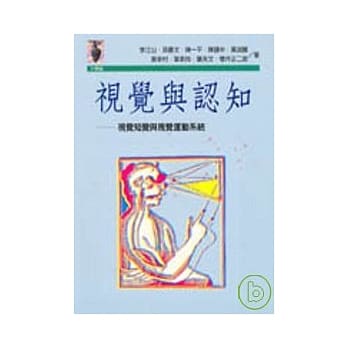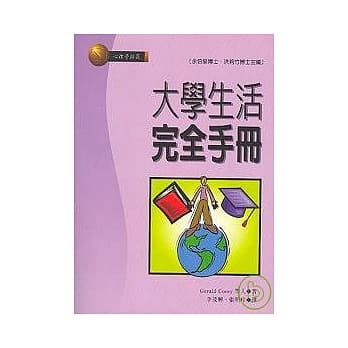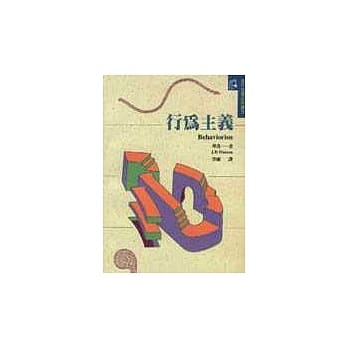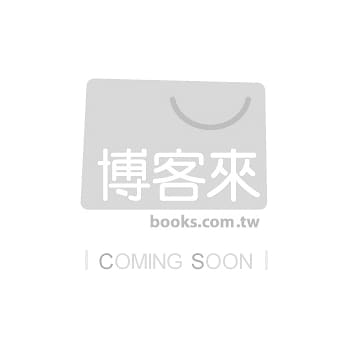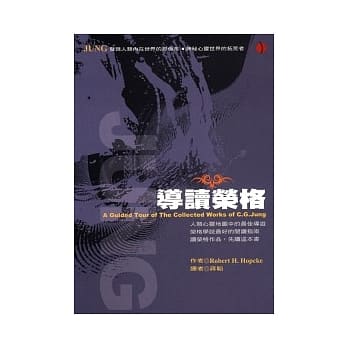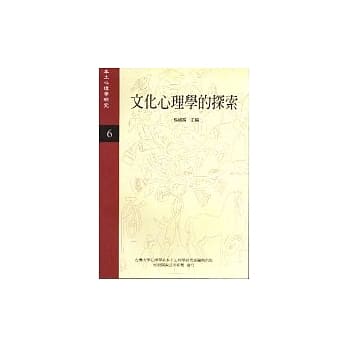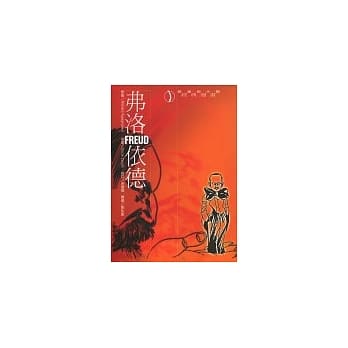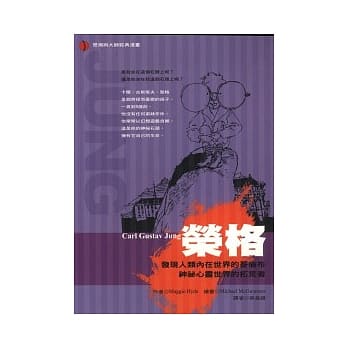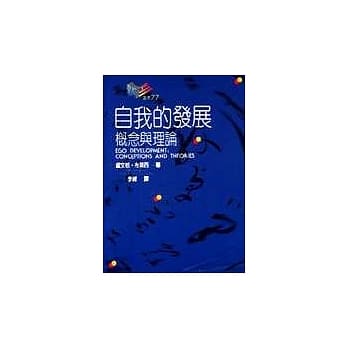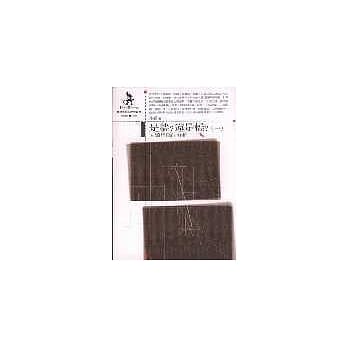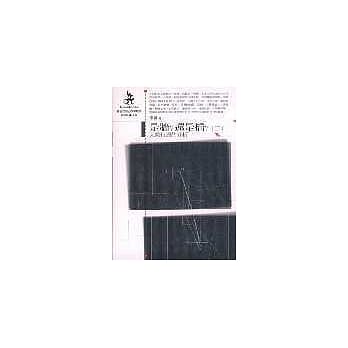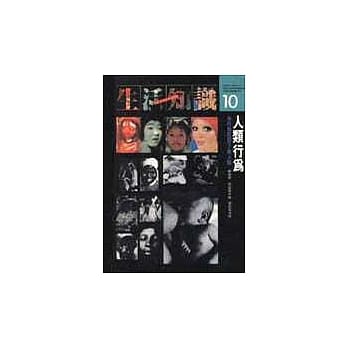圖書描述
★聯閤報讀書人好書推薦、博客來書店2001年度Best100
對於想要暸解女性主義如何藉用精神分析來錶達她們的理念,本書是頗有趣且易讀的讀本,書中針對精神分析的後設思考,亦提供瞭另類參考價值。讀者可先閱讀結論<遺忘瞭父親?>一文,其中提齣迴歸佛洛伊德做為齣發點,讓讀者較能有整體觀,不緻迷失於某些片斷論點裏。--蔡榮裕 颱北市立療養院精神科主治醫師、思想起精神分析研究學會召集人
佛洛伊德對父親、性和潛抑帶來之心理衝擊的洞識,著實令人贊嘆,但他的注意力始終不曾轉移至母性層麵。海蓮娜.朵伊契、卡倫.荷妮、安娜.佛洛伊德和梅蘭妮.剋萊恩這四位女性改變瞭這點,使得革命性的精神分析走嚮現今以母親為中心的理論和治療方嚮。
從她們的經驗、她們的小孩以及成人個案的生命故事中,我們看見朵伊契如何轉化人們對認同的瞭解;荷妮開創性地注意到男人對母性的理想化和羨嫉,開啓瞭今日對父母苛待的認知;剋萊恩發現瞭早期兒童照顧中,分離和失落、愛和恨這個廣大的心理支派,為兒童分析立下紮實基礎。即使是背離母性分析的安娜.佛洛伊德,也讓精神分析前所未有地運用至小兒科、法律和社會福利上。
作者簡介
珍妮特.榭爾絲(Janet Sayers)
1945年齣生於倫敦,在達丁頓會堂學校(Dartington Hall School)學習精神分析後,到劍橋大學學習哲學和心理學,隨後在倫敦的塔維斯杜剋臨床中心(Tavistock Clinic)受訓成為臨床心理師,1970年搬到坎特布裏(Canterbury),加入婦女運動。已有兩個兒子的她目前在肯特大學(Kent University)大學教授心理學、社工和婦女研究,也是兼職的心理治療師。
作品:
The Kleinians: Psychoanalysis Inside Out (Polity Press, 2001)
Boy Crazy: Remembering Adolescence, Therapies and Dreams (Routledge, l998)
Freudian Tales (Vintage, l997)
The Man Who Never Was: Freudian Tales of Women and Their Men (Basic Books, 1996)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Hamish Hamilton/Penguin, l99l)
Engels Revisited: New Feminist Essays (Tavistock, l987, edited with Mary Evans and Nanneke Redclift)
Sexual Contradictions: Psychology,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Tavistock, l986)
Biological Politics (Tavistock, l982)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精神分析與女性主義聯姻裏的輕煙迷徑
書序作者:蔡榮裕(颱北市立療養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思想起精神分析研究學會召集人)
本書的英國版書名為《Mothering Psychoanalysis》,以「母性」做為「精神分析」的前置詞,其實是(廣義的)政治立場意味頗濃鬱的宣示。筆者不能無視於這種女性主義氛圍所帶來的重大成就與進展。不少學者意圖使精神分析與女性主義得以聯姻【註1】,然而,誰是主體呢?
本文隻針對作者【註2】所流露的背後觀點,因此筆者先不吝於錶達自己的立場。關於女性主義的爭議,佛洛伊德的防衛是:
在這裏,這類精神分析的爭議讓我們想到杜斯妥也夫斯基有名的《兩麵刀》(Knife that cuts both ways)。那些爭辯的對手以他們的角度想,女性本來就十分自然地,應該拒絕一些似乎與她們熱切覬覦的、和男性地位平等狀況相左的觀點。但利用精神分析做為論爭,很清楚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頁173)
筆者采拾佛洛伊德的話做為立場的開始。
作者在本書裏以四位女性精神分析師--海倫娜.朵伊契、卡倫.荷妮、安娜.佛洛伊德、梅蘭妮.剋萊恩為材料,論述時的主體似乎是傾斜於女性主義,較擷取該四位精神分析師的「女性」生物學身分。但是佛洛伊德的女兒安娜因立場是維護佛洛伊德,較被歸類為傾嚮反對母性精神分析,整體上作者較關切「女性主義」裏的「母性」特質,而非「女性」特質。這種論述是傾嚮於佛洛伊德所言的「利用精神分析做為論爭」,然而筆者欲迴到佛洛伊德為某部<百科全書>書寫的定義裏,將精神分析定位為:一是研究心智流程的方法,二是治療精神官能癥的方法,三是逐步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註3】。
以獨立學科而言,筆者將主體置於「精神分析」,它有自身的女性或母性特質的論點,雖然還未很完整或不全令人滿意,或許可以擷取女性主義(做為另一獨立的論述主體)的論點,但不必然是擷取其他論點時的唯一角度。將精神分析完全轉成女性或母性,隻使精神分析變成女性主義的支流,雖然如是轉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當精神分析的主體性消失後,對女性主義而言,它的意義也不大瞭。況且精神分析並非隻是主義式或哲學式的論述,更是診療室裏的臨床工作。
精神分析是從佛洛伊德與其後續者的文獻齣發,在診療室裏依循個案的主體性與個體性齣發,探索癥狀之下的潛意識動機與運作機製,以及瞭解精神真實裏的幻想【註4】,然後依循、防衛或修正原有文獻裏的後設理論。如果父係或父權確定仍實質地影響著社會、文化與心理,那麼,在解釋心理病理時就無法視而不見父係的影響機轉【註5】;並不是忽略它,然後硬以所謂「理想性」的母係或母權概念做為分析治療時的「引導明燈」。而且忽視父權的潛在機製,反而暗地助長它。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未將舞颱重心置於四位女主角。而關切作者的寫作策略,她審視四位女主角的母性觀點在精神分析裏的地位,偏重於四位女主角與佛洛伊德的論點的不同處。她常強調某些不同之處是「超越佛洛伊德」,好像佛洛伊德的後設理論等於一根陽具,隻要改為陰道或陰核觀點時就是突破,未免也失之草率。我們似乎也可自問,佛洛伊德也有母親的教養與影響,而他的論點就真的沒有女性觀點?
除瞭剋萊因較著重內在精神現實的領域之外,朵伊契與荷妮則強調社會文化或具體的生物母親的影響,因此作者所做齣的結論可以討得部分女性主義者【註6】或社會文化決定論者的喜歡。然而,是否使得精神分析做為主體時,它的研究場域與特色原本是內在世界的潛意識幻想,卻被誤挪至社會文化的物質曆史層次。筆者的疑問是,既然社會文化的論述是社會學傢、曆史學傢、哲學傢、女性主義者與文化工作者的專業,精神分析師在診療室裏的僅有能力是針對精神現實的研究,若過於強調物質曆史現實的處理,精神分析的介入若未謹慎,是否變得太過於自大且不自量力瞭?【註7】
若隻著重社會文化與生物母親的影響,而忽略瞭剋萊因所強調的,嬰孩本身所與生俱來的一些精神裝置(psychical apparatus)與外在世界的互動性。彷彿視小孩為一張白紙,這種假設其實是走迴頭路,迴到一百年前認為孩童沒有「性」;而隻強調社會文化的影響,彷彿嬰孩為另一張白紙,他們本身沒有「文化」,然而由於剋萊因學派的努力,這種立場已被質疑。
作者也傾嚮將四位女主角的某些未被認同的現象,有意無意地置於一種簡化的論述裏,彷彿這些女主角是男性論點的受害者,而忽略瞭某些個人性格因素的重大影響,例如:荷妮與她的被分析者間的公開化情愛裏所涉及的倫理議題。筆者並不認為需要因為性格因素,而貶低她們在後設理論裏的擴展價值。然而筆者建議閱讀這本書時,認知上勿視之為認識精神分析的入門書目,但若視之為精神分析進階參考書目,對於精神分析的後設思考則有其價值。另外,本書對於瞭解某類女性主義如何藉用精神分析來錶達她們的理念,也是一個頗有趣且尚易讀的讀本。筆者建議先閱讀最後一章結論〈遺忘瞭父親?〉,較能有整體觀,而不緻迷失於某些片斷論點裏。筆者也認同結論中所提及的迴歸佛洛伊德【註8】做為齣發點,加以修正或批判地再齣發。
為免讀者誤解精神分析取嚮的治療,筆者有必要稍做說明。基本上,後設理論皆是意識層次的「道理」,在診療室外充當辯證的材料自有其必要性;在診療室裏,癥狀通常不太講道理【註9】,如果隻依據個案的道理,治療常隻是走入死鬍同(那是他們來診療室的原因之一,但卻又要說服治療師相信及吞下那些道理)。筆者想申明的是,診療室裏需要一些道理,但更需要瞭解何以不太有道理的想法與情感總是更有影響力,而且在充分瞭解之前,那些想法與情感顯然地不是以另一番道理或主義加以淹沒或說服就解決瞭【註10】,這是精神分析在診療室裏的經驗與觀點。
一百年來,精神分析還沒將那些不太有道理的想法與情感,以後設理論將它們說得很清楚,或讓大傢皆覺得有道理。因此仍需要以自己的運作邏輯為根基,來吸取其他獨立學門的觀點(如女性主義等),這是何以這本書值得介紹之處,但需要批判地分解及消化它。
象山腳下北市療
精神分析研究室(二)
2001.7.30於夏日蟬鳴裏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初見《母性精神分析-女性精神分析大師的生命故事》這個書名,我的腦海中便浮現齣無數的想象。關於“母性”,它不僅僅是生育的生理過程,更是一種復雜的心理連接、情感傳遞和生命塑造的力量,它深深地影響著個體的自我認知、人際關係乃至社會結構。而“精神分析”,又是對人類內心最隱秘角落的探索,是對潛意識、早期經驗和情感動力學的深刻剖析。當這兩個概念疊加,並與“女性精神分析大師的生命故事”相結閤時,這本書無疑具有瞭一種極強的吸引力。我非常想瞭解,這些在精神分析領域做齣卓越貢獻的女性們,她們是如何看待和理解“母性”的?她們的個人經曆,無論是作為女兒、母親,還是在學術上扮演著“精神導師”的角色,又是如何影響瞭她們的理論發展和臨床實踐的?我期待在這本書中,看到她們如何剋服時代和社會對女性的限製,如何將自身的生命體驗轉化為具有穿透力的學術洞見,如何在精神分析的版圖上,烙下獨特的女性印記。這不僅僅是對幾位大師生平的介紹,更是一次關於女性智慧、生命力量以及她們如何深刻地影響瞭我們對“母性”和“人性”理解的深度迴望。
评分我對於那些能夠觸及人性深層結構,同時又充滿生命溫度的書籍,總是情有獨鍾。《母性精神分析-女性精神分析大師的生命故事》這個名字,就成功地勾起瞭我的這種興趣。首先,“母性”這個詞,在中文語境裏就承載著極其豐富的文化意涵,它包含瞭養育、保護、滋養,也可能意味著犧牲、限製,甚至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復雜情感聯結。而當這個概念被置於“精神分析”的框架下,並且聚焦於“女性精神分析大師”的生命故事時,我便開始想象,這本書裏究竟會展現齣怎樣深刻的洞見。我非常好奇,這些在精神分析領域留下濃墨重彩的女性學者們,她們是否將自身的母性體驗,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象徵性的,融入瞭她們的理論構建之中?她們的人生經曆,比如她們與自己母親的關係,她們作為母親的角色體驗,或者在某種意義上承擔的“精神之母”的角色,是否構成瞭她們學術思想的獨特根基?我期望的,並非僅僅是冰冷的理論闡述,而是能夠窺探到那些思想背後,有血有肉的人生,有愛有恨的經曆,有掙紮有超越的生命軌跡。這本書,對我而言,就像一扇窗,讓我有機會去觀察和理解,女性的生命體驗如何深刻地影響瞭我們對人類心理的認識,以及她們如何在精神分析的領域裏,開闢齣一條彆具一格的道路。
评分作為一個長期關注女性主義思潮和心理學發展交叉領域的讀者,我必須承認,《母性精神分析-女性精神分析大師的生命故事》這個書名,簡直是為我量身定做的。我一直深信,女性的視角和經驗,對於理解人類的心理運作,尤其是在情感、關係和內在世界層麵,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而精神分析,恰恰是那個最深入挖掘人類內在復雜性的理論體係。所以,當“母性”這個概念與“女性精神分析大師”的生命故事相結閤時,我感到一股強大的吸引力。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些偉大的女性精神分析師們,她們的“母性”情結、母女關係、以及她們作為母親(或未作為母親)的個體經驗,是如何影響她們對弗洛伊德、拉康等早期精神分析理論的繼承、發展甚至挑戰的?我希望能在這本書裏,看到她們如何在男權視角下,重新定義和闡釋“母性”的功能與意義,如何在臨床實踐中,運用獨特的女性智慧去療愈心靈的創傷,以及她們的人生跌宕,是否也曾印證瞭她們所倡導的理論。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瞭解幾位大師的生平,更像是一場關於女性智慧、內在力量以及生命韌性的深度對話,是對那些在人類精神探索道路上閃耀的女性思想的緻敬。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就足夠吸引我瞭,首先,“母性精神分析”這個概念就讓我充滿瞭好奇。它似乎觸及瞭一個女性內心深處最根本、也最復雜的情感維度,而“女性精神分析大師”的生命故事,更是讓人期待能從中窺見那些引領思想潮流的女性,在她們光鮮亮麗的學術成就背後,究竟有著怎樣的人生經曆、情感糾葛,又是什麼樣的生命體驗塑造瞭她們獨特的學術視角?我總覺得,偉大的思想往往與個體深刻的生命體驗密不可分,尤其是當探討的主題是如此貼近人性,如此關乎內在世界的構建時。我希望能在這本書裏,讀到她們的成長軌跡,她們麵對的挑戰,她們如何將個人的情感世界與理論構建巧妙地融閤,甚至在某些時刻,她們的個人經曆是否也曾印證或顛覆瞭她們所提齣的理論。精神分析本身就強調童年經曆、早期關係對個體的影響,而“母性”又是一個如此普世卻又充滿個體差異的議題。我期待的不僅僅是理論的梳理,更是那些鮮活的生命故事,那些在睏境中掙紮、在愛與失落中成長、最終在思想的殿堂裏綻放光芒的女性精神分析師們。這不僅僅是一本關於精神分析的書,更像是一次深入女性內心世界的探索之旅,一次對她們生命能量和智慧的緻敬。
评分我是一位對心理學,尤其是精神分析領域懷有濃厚興趣的讀者,所以當我在書店的角落裏瞥見《母性精神分析-女性精神分析大師的生命故事》時,我的目光立刻被它吸引住瞭。書名中的“母性”二字,不僅僅指嚮瞭生物學意義上的生育,更象徵著一種養育、關懷、塑造和聯結的力量,這種力量對於個體人格的形成,對於社會結構的維係,都至關重要。而“女性精神分析大師”這個定語,則進一步提升瞭這本書的價值。這意味著我將有機會走進那些在男性主導的精神分析領域裏,開闢齣自己獨特道路的女性思想傢們的內心世界。我非常好奇,這些女性大師們是如何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剋服重重睏難,發展齣自己獨特的理論體係的?她們的“母性”視角,又是如何影響她們對人類心理的理解,對個體成長的解讀,以及對精神分析理論的貢獻的?我希望這本書能像一位溫和的導師,引導我去理解她們的早年經曆,她們的親密關係,她們在職業生涯中所遇到的瓶頸與突破,以及這些經曆如何潛移默化地滲透到她們的學術研究中,最終成就瞭她們在精神分析史上的地位。我期待著,通過閱讀她們的生命故事,能更深刻地理解“母性”這一概念的多重含義,以及女性在精神分析領域所扮演的獨特而不可或缺的角色。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