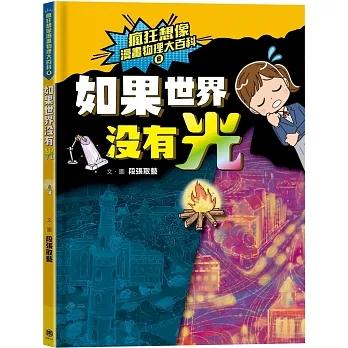序
不信青春喚不回 不容青史盡成灰
鐵路,意味旅途。路軌本來是希望,是溝通遠方的,直至一九七三年,陸軍總司令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於智利發動武裝政變,展開漫長的軍權統治。鐵路軌改變,又維持其涵義。一截截沉重路軌被切下,以鐵線綁到前政府官員、示威者和學生身上,將異見人士永遠送往軍政府賜予他們的應許之地——海底。
海岸線長,成了暴政優勢。據真相與和解國家委員會於一九九一年發表之報告,智利於軍政府執政十七年期間,有二千零九十五人遇害,一千一百零二人失蹤。
首次聽到智利軍政府鎮壓,是一九九三年,讀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講述紀錄片導演密戈爾.立頓(Miguel Littín)的報導文學《智利祕密行動》(Clandestine in Chile: The Adventures of Miguel Littín)。當年因為這書夠薄,才於旺角二樓書店買下。軍權統治與異見者被消失,對那時的我來說,遙遠得像聽維京海盜坐叮噹(台譯:哆啦A夢)時光機回來,暢談掠奪北歐小鎮經歷一樣。怎料廿六年後,竟於我家鄉重演。專業人士、學者教授因政見被革職,外國記者被拒入境,本地記者被無證件矇面警察襲擊,查封傳媒,取締學生組織及工會,民選議員集體入獄,街上一具具「死因無可疑」的墜樓屍體,海上漂著沒鐵軌縋著的,女學生全裸的屍體。
本書緣起於二○一九年八月廿五日,當日臉書專頁「抗爭少女日記」發布了一段視頻,一隊黑衣蒙面抗爭者,與警察衝突後,途經沙田新城市廣場,受到商場內一眾市民的熱烈鼓掌。
我看時,一直流淚。這些年輕人不圖名譽,也無利益。換來的,除肉身傷害,就是牢獄風險。將這群亂世兒女比喻成當代斯巴達人,似乎並不準確。因為斯巴達人從小孩起,就接受共餐組織的地獄式武術訓練。香港年輕人所接觸的射擊或軍事訓練,大概僅限於以兩只拇指按動任天堂遙控器。
香港人走過一樣的街頭,面對一樣的鴻溝;有人沉默,有人發聲;有人繞路,有人殉道;有人苦思自己可為抗爭貢獻甚麼,有人盤算抗爭能為自己帶來甚麼;有人信奉留得青山在,有人豈因禍福避趨之。
各家自掃門前雪,從來是多數華人家庭暗自行推行的國民教育。勇武者走到這一步,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基因改造食物吃太多?漫威電影看過頭?那時候想,該有專業記者或歷史學家,將這些都記錄下來吧。
短短半年,香港迅速葛咸城化。因為種種,我匆忙辭別故土。曾天真以為,只要離開,傷疤自會平復,後來發現並非如此。我常於晨昏蒙影中乍醒,渾渾噩噩呆望窗外等日出。嘗試躲進自己喜歡的報導文學中,來忘掉錯對,來懷念過去。結果,反思更多。
一九一一年,黃世仲在參與黃花崗起義個多月後,便以世次郎為筆名,在《南越報》連載關於起義的報導文學〈五日風聲〉;一九六一年,柏楊以鄧克保為筆名,在《自立晚報》連載關於國民黨孤軍,在泰緬邊境區叢森游撃戰的〈血戰異域十一年〉;一九八六年,馬奎斯撰寫《智利祕密行動》等等。這些傑出的紀實文學都正好說明,敘述反抗者的第一身經歷,與其作戰同俱意義。
因為想上,願上,會上,能上前線的,畢竟少數。
勇武者當時忙著反抗,事後急於逃亡,無暇給大後方同胞逐一解釋細節因由。而這些經歷,卻是民族構成的重要紀錄。歷史沒有如果,只有結果。大眾不需要認同每個行動,但最起碼你在臉書或飯局中下定論前,能去了解一下當事人的說法。
司馬遷寧願捱上痛不欲生的腐刑(閹割),仍堅持苟且存活,皆因《史記》尚未完成。以往不能想像,這種非要記錄歷史不可的決心,也無法想像箇中切痛。二○二○年七月一日凌晨前的幾小時,香港政府宣布,把國安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數小時後立刻生效。條例沒經過立法會審議,甚至支持的香港高官,也坦誠從沒未看過其中內容。由法例生效那刻起,香港人經歷了一次精神腐刑,部分思緒脈絡被切除了。從此說甚麼、寫甚麼、做甚麼,得小心翼翼,誠惶誠恐,過去的自由奔放,俱成歷史。古云崖山之後無中華,禮失求諸野,海外飄散港人,實有道德義務去溫存這段民族記憶。
想起當日視頻,掙扎要否獻醜動手。我有一百個避寫理由,卻只一個堅持原因,就是不容青史盡成灰。結果盲打亂撞,試將構想落實,幸遇海外朋友協助,開始與各地流亡者接觸。
訪談從二○二○年夏季開始,考慮各因素,決定透過中間人核實身分。確認後,我與受訪者均以化名溝通,我不知對方真實姓名,受訪者亦不知道我是誰,這樣比較能互相保護。感謝台灣保護傘組織支援與協助,聯絡並核實每位流亡的受訪人士。
採訪一般分好幾次進行,因為要是簡單把訪談壓縮在一兩小時內完成,會讓受訪者容易因有時間壓力,於是給出較為標準的既定答案,盡可能提供一些他/她自己認為,需要向大眾傳遞的主題訊息,內心就難免先會對內容進行自我篩選。所以我更傾向聊天,每次約一至兩小時,不設特定題目,讓受訪者隨意說,可以從最近的生活或電影聊起,一直說到抗爭、感情、家庭。
也許部分抗爭支持者會認為,前線手足在衝突中做過甚麼,不應大肆宣揚,以免被警方和中共抓著把柄。尤其勇武的自述,隨時可能成為罪證。
從運動一開始,就有不少人提出,需尊重前線抗爭者自行作出的決定,不適合給予太多意見和干預。同樣,當流亡手足同意將經歷公開,支持者亦無須對此過分緊張,或急忙作抗爭糾察。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把經歷說出來,固然有一定風險,但政權更樂見這些記憶不被提起。以七二一元朗恐襲事件為例,當能夠公開表述的說法越來越少,當網上片段不停被社交媒體刪除。權力一方,就有能力把記憶肆意扭曲,從「鄉黑向市民發動無差別攻擊,警方配合袖手旁觀」的方向,逐漸淡化成「兩幫不同勢力人士互相打鬥」,甚至以暴動罪,把受襲一方告上法庭。別小看這種對歷史記憶的扭曲,我們看過當時直播的一代,肯定忿忿不平,皆因清楚真相與歷史。但當政權佔據所有主流媒體和敘述渠道,三五年後的下一代就會說:「我爸媽和學校教科書都各執一詞」。再三五年,真相就被模糊。所以他們發聲的書面紀錄,與抗爭同樣重要。
過去媒體對前線勇武的描述,容易陷入臉譜化。政權有他的「黑暴」固有形象,刻意將其扭曲醜化;同時支持者亦有其英勇和「睇吓我哋手足有幾乖」之圖騰須維持。雙方難免陷入各取所需的演繹。寫這些故事前,我沒特定目標,只希望盡可能忠實呈現受訪者的狀態,因此本書內容,部分可能不如支持者般預期,或公眾對勇武形象的內心投射。
書中提及的受訪者年齡,以第一次訪談時的歲數為準。
鑑於大部分受訪者均有被捕風險,所以即使他們願意披露細節,我仍希望以其身分保密為前提。為此,我願意讓出文章部分的自主及完整性。採訪前,我向各人承諾,完成初稿後,會讓當事人審閱,如果他們讀後希望增刪,我均願意配合作修改。我認為這樣,能助當事人放鬆,無後顧地說出最真誠感受。好幾次,受訪者隨便聊天時,說了一大段,完後才醒起:「這些好像不要放進去吧。」我說別擔心,所有內容最後你還可再次確認,先聊就成。後來我拿出初稿時,會特意提醒,這段是你當時說過不要用,但我認為放進去,更有助表達你的想法。你先看,要是讀完仍覺得需要拿走,請告訴我,我就拿掉。結果很多次,當事人看完後,又覺得其實說了也無妨,於是同意保留。
也許有讀者會對當事人講述的經歷,其真確度有所懷疑。但從來,口述歷史也只是時代的橫切面,並非歷史全局。我們透過當事人具血肉的親身經歷,試著構築主流媒體窺探不到的角度。對於當中有否偏差,只能留給讀者自行判斷。
謹願此民族列傳可溫存記憶,他日煲底榮光時,後世能銘記先行者們以死相搏的氣宇與血汗。
二○二一年九月廿二日
給平裝版讀者的話
有次朋友喝醉時告訴我,人生有三個逃不了的階段,那是出生、辱華與死亡。我說,這是我見過你最清醒時候。
身為香港人,以華文寫作,自然逃不過辱華詛咒。因此我有義務提醒正捧讀劣作的閣下,不管你身處書店、咖啡室、舊書攤或家中,閣下之錯愛,已可能將讓你跟我一樣,邁進人生第二階段。或許你現在因身處海外,所以比較放鬆,但根據香港政府二○二○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宣稱擁有香港以外的全球管治權(不確定是否包含全宇宙,或元宇宙),所以各位往後海外吃中餐,不論上餐館還是叫外賣,都得加倍?慎,尤其留心那些幸運餅乾,因為你不會知瓣開時會拿到甚麼,字條上也許印著:辱華!你已煽動他人仇恨國家!國安法!
我得承認,自身對失去自由有所恐懼,尤其係失去早上可自然醒之權利,所以才怯懦地選擇匿名抗爭。香港地有比我更勇敢的創作者們,實名的以羊與狼之兒童繪本故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人如何跟極權對抗。她們是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的黎雯齡、楊逸意、伍巧怡、陳源森及方梓皓。香港政權控告她們以童話繪本,煽感他人持續反抗,引起他人對香港司法及中央的憎恨,導致喪失國家認同感。她們因為那些羊和狼而入獄十九個月,組織亦被迫解散。亂世之下,我們都是盡力保持善良與信念的羊。是她們之勇氣,點下了燈,照耀在幽暗中前行的我。沒有她們,我不會開始寫這書。
從國安法還未公佈,我就與團隊著手,籌備這採訪報導計劃,正是因為預料風暴將至,極權高壓與挫敗感之下,人們將無奈轉入沉默與遺忘。這些,我們阻止不了,也無權阻止同行者意興闌珊,回歸生活,但這些前線無名手足的事蹟,還是值得被有系統地記錄下來。唯獨書寫,方能與遺忘和系統刪除對抗。
每個人選擇面對極權的方式都不一樣,提出「當你對抗惡魔時,小心你自己變成惡魔」的是尼采,但對這箴言最落力的推銷員,很可能就是惡魔自己。因為惡魔最需要的,就是你有底線。而勇武,就突破了這思想枷鎖。在此,我不算花唇舌來強調,前線抗爭者有多器宇軒昂,因為接下來你將能體會(假設你沒打算放下這書的話)。
二〇二二年夏天,本書首度由一個流亡來台灣的港人小組織,獨眼科技傳媒出版社發行限量的硬皮精裝本。編輯問,可否寫段簡短自我介紹?為拿捏平衡讀者與國安公處之間的求知欲,我苦思糾纏了數天,才戰兢交出一小段:
前半命好,衣食無虞,樂得逍遙,好讀閒書。竊以為可玩過世,惜逢我城劫難,方始睡醒,驚覺禮崩樂壞之時,我們渺小得似螻蟻飛舞。結果從離地走至鍵盤,從課金殺到埋身,半推半就上梁山。後倉皇去國,一闕遺憾;百般滋味,客途秋恨。唯以筆頑抗,不讓青史盡成灰。望他朝滴水穿石,淘砂爍金,愚賢互見,忠奸漸辦。
編輯回饋:可以再⋯⋯具體啲?幾乎寫咗大半生啦喎我話。最後,出版社沒用上,另找高明代勞。從來,寫他人易,自我描述難。香港人對抗爭亦是如此。
因為無大台式的如水抗爭,所以抗爭陣型門檻⋯⋯好吧,是幾乎沒有門檻。當中難免良莠不齊,但我們從不願承認,甚至為求團結大多數,常常出現護短與冷處理。於是間接助長機會主義者和社混祈福黨的滋生,這不是政權抹黑,而是確實存在的兩難。港共黑警,固然惡貫滿盈。但抗爭陣營,又何嘗不是充斥投機分子與騙徒。
當年記者會上長嘯:「我準備咗一百副棺材,九十九副留俾禍港土共,一副留俾自己」的,如今早已覺悟前非,華麗轉身成污點證人,天天證人欄內為隊友遞棺木;當年豪言帶領自己友遠征元宇宙,要買地爭取言論自主空間的,亦已透過網上販售虛假陳述的投票權,掠個幾千萬,爭取到其個人海外豪宅的自住空間了。
世人記憶體載量有限,以上種種,即使未至空白,早已化成都市傳說,莫衷一是了。而正正因爲充斥著變色龍,才突顯出勇武的高貴與堅毅。
當然,亦並非每個滯留者均悲觀消沉。去年本書作小規模私下出版後,據悉一些仍潛伏香港的堅定分子,私下把這精裝本以「自己方法」送抵香港,供有心人分享。結果事情曝光,惹來建制派媒體的口誅筆伐,甚至把相關組織及本書向國安公處舉報。此事我沒參與,但團隊仍為此深感不安,紛紛找我查詢,問是否一切安好。對此,我都一概回應:係咩?碰!
但願每位香港人,及世界各地仍面對打壓的藝術工作者,繼續在艱難時刻中保持幽默。如同艾茵.蘭德(Ayn Rand)的小說《源泉》(The Fountainhead)所言:「一個人失去了幽默感,就失去了一切。(One loses everything when one loses one's sense of humor.)」而我,於爭取自由和民主的路上,將盡力保持每天睡到自然醒;在抵達人生必經的第三階段前,恐怕得在第二階多蹓躂一會,好長的一會。也希望你會喜歡這個平裝本,它沒有硬皮本那麼重。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